贺观张老八十寿(马国馨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院顾问总建筑师)
马国馨
今年(2013年,编者注)3月19日是著名资深建筑师吴观张先生的八十大寿。作为他的学弟和共事多年的同事,谨以这篇短文为他贺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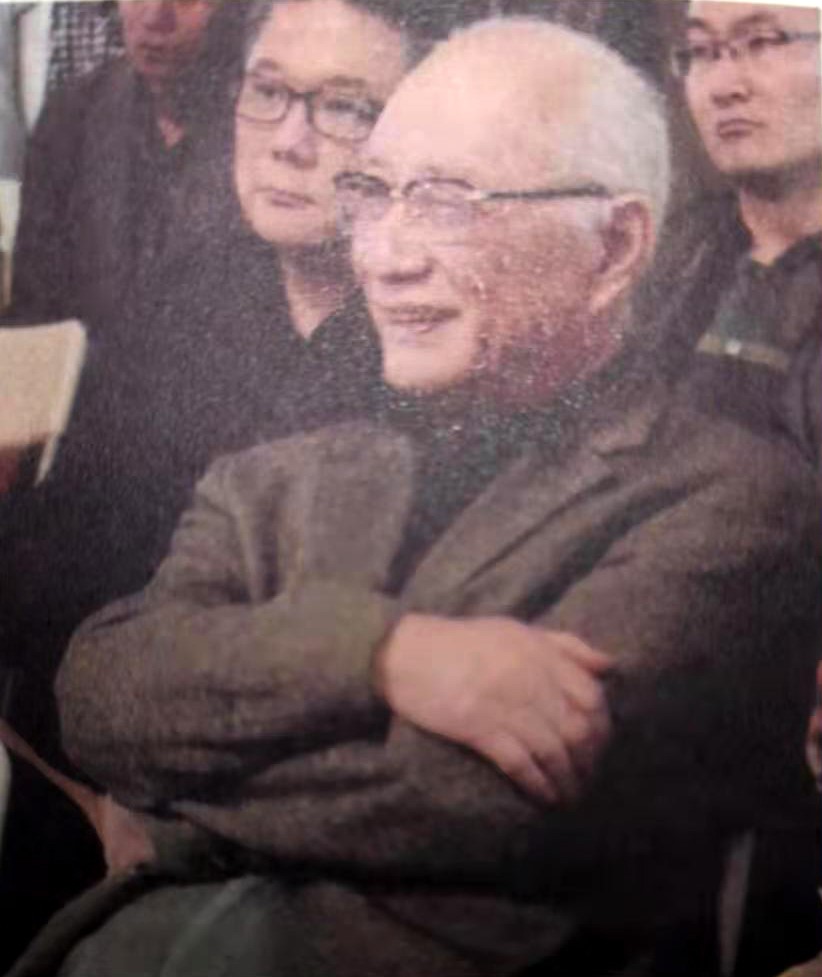
吴观张学长,2013年
建筑业内人士对吴观张是十分熟悉的。他已为这个行业工作了近60年,在许多方面均有建树。但若不从事这一行,可能对这些就不那么了解了。所以先摘录一段他的简历:吴观张,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1952年苏州高级工业技术学校土木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53年调入江苏省教育厅从事设计工作。1956-1962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1980-1984年任院长,1984-1994年任院副总建筑师,1994年退休后回聘,任院顾问总建筑师,2005年后受聘为北京筑都方圆设计公司和五合国际集团任顾问总建筑师至今。
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文字也还源于老吴的一句玩笑话:此前我曾陆续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回忆已逝去的建筑界人士的文章。有一天老吴遇到我就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要写我那就趁我还在时快写,免得我以后看不到。”其实我写那些文字的出发点都在于那些人在世时都曾经为国家、为行业做过许多贡献,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理应为人们所纪念。可是在当下一味追求物欲的大环境下,那种“人走茶凉”让人觉得很不是滋味,所以不得不一吐为快!像 2001年是建筑设计大师张镈先生的百年诞辰,他在世时为首都留下了像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友谊宾馆等经典作品,按说有关方面应有所表示,可最后就那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只有他的家乡山东无棣县政协委托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40万字的回忆录《回到故乡》,并邀我题写了书名。我除了曾写过一篇《长留念记在人间》的回忆文章外,也就只能做这点小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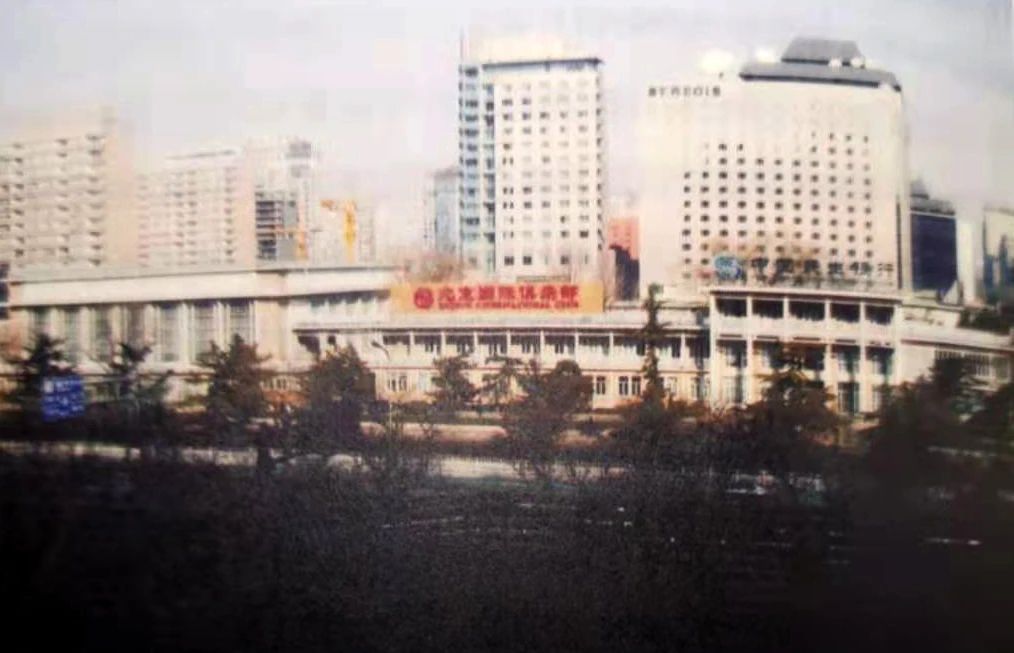
建外国际俱乐部
当时三室承担了这一任务,由老吴任这三个项目的工程主持人,我担任了国际俱乐部项目的建筑负责人。现在看来这个项目只有1.4万平方米左右,算不得什么大工程,因“文革”期间很少有民用项目上马,所以在当时还是很引人瞩目的。老吴除了协调三个子项的总体工作外,还在俱乐部工程中亲自绘制了许多施工图纸。当时是宋士芬负责一段网球馆,刘永梁负责二段台球、棋牌、理发美容,我负责三段餐厅、宴会、多功能厅,老吴负责四段电影厅。那时张镈、张开济二位老总也刚刚出来工作,在方案阶段曾以顾问身份参与过,但主要还是由年轻同志来完成。我是第一次承担这样高标准的民用建筑,心里没底,所以很是紧张。但老吴十分信任地放手,使我在实践中有了锻炼的机会。我们除了在现场向施工单位的翻样师傅李大毛等人请教学习外,在设计上也一起想了许多办法,好使设计有所前进、有所创新。这里有立面上的处理,用马赛克和水刷石的搭配表现传统的插枋形式;在内部装修上采用简洁明快的处理,不用过多的线脚;与工艺美术家合作创作了一批国画、漆画、镶嵌、玻璃画等形式;自行设计制造了一批新型灯具……总之还是动了不少脑筋。我也就是在这个“三边工程”的实践中,从不懂到粗知,学会了好多东西,也增长了后来主持工程的自信。俱乐部完工以后我就独立主持了东交民巷15号宾馆为西哈努克亲王所用的游泳馆和多功能馆(可用于打羽毛球、看电影、开招待会等),在工程将竣工时,因院里派我去农村做知识青年的带队并劳动锻炼一年,又是老吴帮我把这一工程圆满收尾,并得到邓颖超同志的表扬。

建外友谊商店
与老吴的再次合作就是1976年的毛主席纪念堂工程了。那时老吴已经是第一设计室的副主任,我是第六设计室的副主任。因为建院将承担纪念堂工程的主要施工图任务,所以院里很早就抽调了四位副主任和一些得力人马,组成了纪念堂设计组。9月14日全国抽调的专家在前门饭店集中解决方案问题时,徐荫培、方伯义和老吴就在那里参加工作。在几轮方案优选集中并经中央批准以后,我们的设计组又长期战斗在工程现场,当时除徐荫培任主持人外,其他方面是这样分工的:徐荫培负责与外部各单位,包括地上、地下的总协调工作;老吴负责外立面设计;方伯义负责室内几个大厅包括瞻仰厅的装修;我则在完成纪念堂基本土建图纸后,负责与现场各施工单位的沟通。老吴他们在外立面琉璃的设计与加工、装饰纹样的确定、红色台基花岗石的选择、廊柱花岗石的选择与加工等方面费了很多心血。多少日日夜夜的共同战斗保证了纪念堂在1977年5月竣工并于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时对外开放。老吴在建院最风光的事我想应该是1980年经民选当了院长。那年市城建工委不知怎么想起要在建院民主推选院长,可能上面原想也就是走走过场的事,并早已提出了院长的人选。可不想下面却把这事当了真,又推出了老吴作为另一名院长候选人,结果最后老吴当选,这也是建院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民选院长。这说明老吴的为人、能力、敢坚持原则、敢为职工讲话等个人魅力得到了全院职工的认可,为大家所信任。老吴当政期间正好我有两年去日本进修学习(这个机会可能也是他那一任做的决定),所以详情不太了解,只从有关材料上看到他就任后加强、健全了技术管理体系:所有的项目分院、室、组三级进行责任制管理;为保证技术力量的后继有人,与六所知名院校签订代培120名毕业生的协议,并支出培养费150万元,还为建院引进了一些人才;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世界建筑》,从财力和人力上支持了这本杂志;在上级单位的支持下,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在他任内先后为528户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解除了广大职工的后顾之忧。因为建院的住房欠账太多,分房要论资排辈计分排队,那时上大学的几年不计分,清华的六年学制就很不合算,所以我并未赶上这几轮分房。但我仍要感谢老吴,因为如果不是这些老职工先分到房,我在后面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的(我是1987年才从筒子楼里搬出来的)。他在任时的作为我也说不全,但有一条,他没利用这个职位在荣誉、待遇、获奖等方面为自己谋过私利,这是极不简单、很值得称道的。可这样的院长也只干了一任,1984年他就离任了,个中缘由并不清楚,只是传说因为他是“民选”院长,所以在平时对上级领导常有顶撞之处,不那么听话,因此并不被领导喜欢。
从院长岗位下来以后,老吴就转向了副总建筑师的技术领导岗位。早在一室当领导时他就组织了室里对体育建筑的研究,在工程实践的基础上由张德沛、李哲之、刘振秀、韩秀春等同志编写了《体育建筑设计》一书,由秦济民和老吴二位室领导最后审定,并于1981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不但是当时国内第一本系统全面地介绍体育建筑设计的工具书,对指导全国的体育建筑设计起了重要作用,也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各种类型的建筑设计指南中的第一册。在为召开亚运会而建设的场馆中,老吴又是我负责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工程的顾问,尤其在方案阶段倾注了大量心血,为自由活泼的总体布局的确定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另外在旅馆和住宅设计上,老吴也有许多建树,有许多研究成果和论文发表。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首都宾馆也是老吴主持完成的,除了满足接待国宾的众多功能要求之外,在运用现代材料表现传统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后来因为我常年在工程现场,所以和老吴的交往就较少了。老吴对于年轻建筑师的成长也是不遗余力地提携和帮助。早在一室时,他就亲自主持方案创作小组,其中的成员当下都成为院内院外行业的技术骨干,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后来老吴又和王昌宁顾问总建筑师一起组成了建筑创作组,每年从进到建院的年轻人中挑选一些苗子,通过方案实践提高他们的设计能力,在创作组的1 1年中也培养了大量人才。从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有亲身体会:在建院这样竞争十分激烈的大环境中,如果没有老吴的大胆使用,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帮助,如果不是他给创造了一些好的条件和机会,如果没有他在各方面的关心,我不会那样顺利地熟悉业务,逐渐掌控全局,经手一些大的重点项目。想起这些,真是十分感激。
老吴在生活细节上也很关心我们。1971年我的孩子出生不久,他就到筒子楼来看望。由于孩子的脸比较圆,老吴就开玩笑说:“脸的长度不够。”当时老岳母听了很不高兴。等孩子长大以后因下颌关节发育不好,脸越长越长,于是我们又埋怨都是老吴那句话给说的。我到日本去学习时,我爱人一人带着孩子,生活上有很多不便,老吴也曾多次询问她要不要调到建院来。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中,我是第一次称呼老吴为“观张老”。按说80岁已是耄耋之年,叫“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老吴仍是精神矍铄、红光满面,跟大家谈笑风生。有一段时间他的腰不好,走路一瘸一拐,还坚持上班,有人还开玩笑叫他“瘸总”,但后来动了手术,十分成功,老吴又焕发了青春活力。虽然对老人祝寿习俗是“过九不过十”,但在他八十华诞时,仍祝福我的老领导、老学长、老朋友青春永驻,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2013年2月15日(春节假日)
(本文原载于《中国建筑文化遗产9》,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