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记保险赌场---刘文彩
“和记保险赌场”据已故彭余罄先生(原宜宾民国时代某煤油公司经理)撰文回忆:民国时代,宜宾商业中心的栈房街、走马街、外南街交汇处的十字口,有一火神庙。庙后面有临江大茶楼一座,为“和记茶楼”,时黄桷夹荫,风景清幽,素为群众休憩之所。(“解放后”已拆除)刘文彩于1930 年在这里开设“和记”赌场,由其宠妾凌君如的父亲凌友臣任总管。为了招徕顾客,发展赌业,设法消除赌徒们的疑虑,特别制定了“赌场安全三项条例”作为“保险”:一,不准赌假;二,不准赌赖;三,不准捣乱打架。并规定,如有违法者,格杀勿论。刘文彩还命令手下的侦缉队长杨绍林、陈德芳、潘海云三人,轮番派便衣队员数人,协同凌友臣的打手驻场维护安全,甚至不惜采用残忍凶暴的手段,下令杀人,以树其威。有一次,一个无赖在赌场赖帐还打人,当即被当众拉下河边格杀。又一次,刘文彩十八团内的军士二人在场捣乱,打手们鸣枪追捕,二人逃至江岸,扑入河中逃命,便衣队也登上小舟,追至中流,开枪把二人打死于水中,还将二人左耳割回,吊在“和记”赌场示众。就这样,“和记”赌场的声誉便传开了。赌场的“名堂””主要是“红宝”、“摇摊”、“牌九”、“单双”,有时还有“骰子”。以“红宝”赌得最大。安有“活媒子”,引诱农民上钩参赌。赌场内摇摊、单双、骰子的长案十八张,包干与职业赌徒肖某、王某、李某三人。规定:每日进“捐款”五十元,递交护商处,此款按日计征,无论赌客多寡或有无赌客上门,天天限交不误。一年便搜刮银圆一万八千多元。而刘文彩把每天收入这五十元作为旧公馆内开支。据传,封建专制王朝,崇文门税捐收入是作皇帝娘娘的花粉钱。因此,有人把这五十元讥为“送交北京”崇文门的税捐。“案子钱”,红宝、牌九是按场收,摇摊或单双则按桌收。当时红宝每天大致赌现钱宝2—3场,每场收案子钱5—10元,免清宝每天有5—6场,每场收案子钱20元,仅此一项,每天约收150远左右。单双案子约40—50张,每张收案子钱3—5元,这一笔则每天收入在200远左右。“案子钱”由刘文彩的心腹袁癞子(名海清,营长)坐守专收,每天所收“案子钱”,送到新公馆,交新太太凌大。此外,牌九每天有四场以上的头钱收入,这些都没计算。“红四黑四”,各种赌博都要抽“头”,有“红二黑五”(输家赢家分别抽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五的头钱,也有“红四黑三”。“摊摊宝”明说不抽“头”,但仍要交“案子钱”,而赌客也有输的。“和记”实行的多数是“红四黑四”抽头。比如,用10元押宝,只能下9.60元的赌注,预留百分之四的头钱,输了则去掉10元,赢了是9.60元。然后又从这9.60元中抽去“红四”的头钱0.38元,实际便只有9.22元。这种“内扣”盘剥,每场如以千元的输赢计算,一进一出,便可收80元。这笔“红四黑四”的头钱,刘文彩要先提一半,因为他是后台老板,宝官是向他接头,由他垫钱支付“红片”,其余一半,先提“案子钱”,然后是赌场开支,付给宝官、宝吏、片官、短片等人的工钱。据老“台家”肖某谈,当时红宝的头钱收入最多,比摇摊、单双的抽头多一倍。场内还设有一种“摊摊宝”,用三颗骰子摇,引诱青年小孩们去赌。“和记”赌业兴旺之后,即招来大批乘机盘剥赌客的吸血鬼。其中最厉害的要算在赌场内放“关钱”取利。放关钱的人多,关期也有多种,有放十天关,二十天关,三十天关,还有放六十天关和放一百天关的。关钱趸借零还。例如借十天关的十串钱,每天还一千一百文,十天还清,共还十一串。放关钱的老板多数是袍哥舵把子的老婆,某队长,某军官的太太,都是“歪人”。 赌场内附设小押当两家,一名“和记”,一名“德利升”。实行的是当钱一千预扣六十文的“规矩”。还有些人在现场用低价现金收买当票、衣物。有的将本钱输光了就把身上的衣裤作押头。结果当然是一切输光,结帐之后,赌棍们要输者立即拿钱,否则“对不起”,输者被请到楼下茅厕里“换龙袍”,即是将全身内衣裤剥光,用两张草纸往他身上前后一贴。被“换龙袍”者不好意思就这样走出去,只好躲到天黑才悄悄回家。彭余罄的一个堂兄(安阜渡口船工)就经历过这样的狼狈。“和记保险赌场”到1932年冬,刘文彩撤离宜宾,凌友臣等再也无法“保险”才收了招牌。但赌博之风仍然盛行。
“企业家刘文彩赚的钱固然不少,与税捐大员刘文彩搜刮的民脂民膏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刘文彩搜刮的手法,与四川其他军阀的搜刮手法大致相同,一为田赋预征,即把以后若干年的田赋提前征收”(笑蜀语)。有关资料记载:在刘文辉统治宜宾期间,戳至1932年12月败退时,田赋已预征到1949年度,预征达17年之多。当然,不仅是刘文辉,有资料披露,以1935年为基准,刘湘的21军多征40年,征到1975年;田颂尧的29军多征52年,征到1987年;杨森的20军多征54年,征到1989年;邓锡侯的28军多征56年,征到1991年。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更离谱,1935年竟预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几乎等于一代农民纳了三代人的‘公粮’。“第二种搜刮手法,是统税杂捐。四川最大的盐场及产糖区,均为二十四军据有,盐税糖税虽由各派提用,但近水楼台先得月,二十四军自然油水最多。”川南关卡林立,往来客货须缴纳所谓“护商税”。“不论是经水路还是陆路来的货物,动辄纳税十余次或数十次。如水路从乐山至叙府,仅二百余里,有关卡三十多处,价值五百元的山货,要纳税四百多元。陆路由内江至成都仅四百公里(应是四百余里——笔者注)有关卡五十余处,价值三百多元的货物,要纳税三百元左右。宜宾县一地设有关卡五十处之多。宜宾城中心设城验卡,东门、大南门、铜湾头(应是潼关码头——笔者注)设四门关卡。各关卡由乡兵把守,‘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使得商民畏兵如虎。”——笔者虽不是内行,但起码的常识还是有的。价值五百元的山货要纳税四百多元,价值三百多元的货物要纳税三百元左右未免太离谱——商人做一趟生意,姑且不说赚钱,至少本钱得拿回来噻!总不至于赔本学雷锋吧?况且,鸡肚子都榨瘪了还能生蛋吗?“‘护商税’而外,还有户口派款、临时派款。户口派款按月征收,下达指标后,‘一伙爪牙又加额分派,从团、保到十家排的排首均有分润’。原定税额因此在征收过程中如雪球越滚越大,民不堪负。临时派款名目繁多,如所谓‘公路费’、‘街道马路费’、‘码头捐’、‘国防捐’等等。‘国防捐’数额最大——派款总数达一百万元,约等于宜宾全县五年粮额。刘文彩为此专门设立‘征收委员会’,以宜宾县县长张伯英为主任委员,张衡先为副主任委员。召集全县民团首领和商会会长在中山街抚州馆开会,刘文彩亲自到场,宣布各乡镇派款比例:城区二十万元,由工商户分摊;剩下八十万元,由各乡镇按田租分派,每担田租派一元。准许经手人从中提取百分之五的回扣。不料仅过月余,二刘大战爆发,叙南动摇。除城区二十万元经刘文彩天天催逼,商会会长鄢之敏、副会长汪体泉不能不提前缴清外,各乡镇都借故拖延,直到刘文彩败退时才交足半数,其余一半装进了各乡镇官绅的私囊。刘文彩征税的具体数目,《刘文彩罪恶的一生》说是每年一千二百万元,此说不可信——四川头号苛杂刘湘,最高年度税额也才一千一百万元(黎英《军阀刘湘的财政搜刮》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倒是《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较为真实:‘要统计刘通过税捐方面到底每年在宜宾——川南搜刮了多少钱财是不可能的’。虽然已不可能统计具体数目,但二十四军之兵强马壮曾居川军之首,所需军费主要出自刘文彩征收的川南税捐。具此算来,刘文彩川南年度税额当仅次于刘湘的年度税额,约近一千万元。”
“最盛时期,我这个集团的文武干部,包扩十几个省籍、欧美、日本各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南北各大学的大学生,无所不有。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而且要花大量的钱。因此,财政问题又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我在这方面,当然也是‘当仁不让’。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摘录刘文辉著作《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3页)这是刘文辉的理由。
宜宾的房产和田产 据刘文彩庄园档案67宗D16卷:刘文彩退居安仁后,仍在叙府拥有巨额房产,街房380多间,独院30多个。合计约六万平方米。刘文彩派人常驻叙府收取房租。笔者于2008年9月1 日去宜宾市档案馆查阅刘文彩相关资料,因宜宾市档案馆是“解放后”1966年才建立的,现存的相关资料不多,或者还未整理出来,无非是一些只言片语。诸如:“(刘文彩)欠交四九年(1949年)公粮甚多”“( 刘文彩)1949至1950年有公馆民房三百余间…….请示:代管、出售,有捐赠作为学校、慈善机构”。一张1950年春季宜宾县(市)征收房捐赋册的统计《宜宾市房屋占有性质表》中表明:宜宾城全城共有房11857间,刘文彩占有272间,其中东城154间,北城20间,西城12间,南城31间,中城55间,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二九。仅次于祠庙会产(百分之二点三六),而永生公馆、天主教堂、仁德等外国教会的房产占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九二,多于刘氏房产的两倍。(《宜宾市志》1992年出版第721页)记载:“1925年起,他(刘文彩)先后在宜宾城内新建了三座大公馆,在修建中山街公馆时强行拆除民房面积一万平米以上,并逼迫公馆对面一吕姓镶牙馆将四层楼拆矮一层,以免窥视其所作所为。”而宜宾县90岁的资深文史研究专家李仲龄(刘文彩的干儿子)却提供了一份不同的资料,他在其《赖烟王——一个鸦片为害的佚事》一文中引用了欧阳霭周(宜宾县人,曾任靖国军支队长、高县县长,宜宾“清铭公、”袍哥大爷——笔者注)讲述有关赖烟王的故事:“赖烟王”是清咸丰末年宜宾城内赖姓富户的独生子(未传其名),家住学院街(中山街)小碑巷,巷内数十家铺房,九成属赖姓所有,还在城内经营多处杂项生意,家财总计不少于十万两纹银之数。他从小受父母娇惯,不学无术。青年时代即染上阿芙蓉癖(即鸦片烟瘾),吸的是英国商人走私来的印度产“人头土”(包装上印有人头像,故名)煮成漂烟(不加烟灰熬煮成烟膏)。他的烟瘾大,一个月要耗烟土百两之多,人们逐以“烟王”称之。烟王的父母谢世后,由他接管家业,他仍整天卷缩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家产、生意全委托给“管事”去管理。由于管理人员的贪污舞弊,生意只亏不盈,相继息业。专靠房租收入来吸烟,根本无济于事,只好变卖产业维持,不到二十年,坐吃山空,房地产当尽卖完,连住房也出卖了。最后沦为乞丐,死在走马街南华宫广东会馆戏台脚下。……“到了民国20年(1931年),刘文彩在小碑巷(实指中山街的大碑巷与小碑巷之间,人们习惯称中山街公馆)修建‘新公馆’其旧址即当年‘赖烟王’的住宅。修建中,从地下挖出鸦片烟灰十余挑,已枯朽无用。”此文佐证了刘文彩当年中山街“新公馆”是在“赖烟王”赖公馆的旧宅上修建的。刘文彩是怎样将其弄到手无法知晓,至少对刘文彩“强行拆除民房面积一万平米以上”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在李仲龄的记忆里,“新公馆”大门开在小碑巷中间段,麻石排坊,门额为“紫气东来”四个黑体楷书大字,大门雄伟气派。进院门右边倚墙筑有一幢两层小楼,大多为高大的平房,檐柱也很大,还有一个网球场,几进院房记不得了,总之,很宽。当年刘文彩撤走后,刘湘属下潘文华部周瑞麟团曾驻扎里面。“解放”初年为宜宾行署驻地。据“宜宾通”陈星奎先生回忆,“新公馆”正门开在小碑巷偏西面,一条巷子进去,门脸一般,比院房稍矮,青砖院墙;大碑巷和中山街也有门可进出。院子很大,西面一直抵拢都长街永生公馆,即现在的广播局。内有院子不少于三重,有正房,有厢房,有回廊。正房是平房,高大;院坝铺有石板。刘文彩撤走后,刘湘舅子周成虎属下进驻,开设蜀丰公司,(面粉厂开在北门陕西馆)。“解放后”,曾为宜宾首任专员许映辉办公住地。1957年苏联专家来宜帮助修建岷江铁桥,还在里面为苏联专家举办过舞会。再后,因城市改建被拆毁了。儿时家住大碑巷的侯正鹄先生回忆:该公馆在大碑巷至小碑巷之间,约五开间,退进街面一公尺,白壁,八字朝门。儿童时代,他曾在邻近的院里爬树玩,从树上望见该公馆里有大坝子,平房很高大,柱头也大。他还记得,对门吕氏是二楼一底的青砖西式楼,二楼三楼临街都有走廊,玻璃窗;门面有三开间宽,中间开大门,大门与对面“刘公馆”的大门不正对。李仲龄告之,这座华居落成后,刘氏家人从未搬进去住过。笔者推测,此华居于1931年才修建,刘文彩次年年底就仓惶撤离,也许华居还未竣工,即使竣工了还来不及搬进去住。笔者于2009年4月21日下午电话采访刘文彩的二子刘元华。刘元华是这样回答的:宜宾只有两个公馆,即粮房街公馆和冠英街公馆(为凌君如置的)。至于让对门楼房拆矮一层,听说有这事,是阁楼,好像是在冠英街,但不是因看得见跳裸体舞。刘元华说话平实、简洁。刘元华理解的“公馆”是主人家居的院宅。如此看来,真正意义的“公馆”只有两个,即粮房街公馆和冠英街公馆。《地主庄园沧桑录》作者周东浩在文中写道:(宜宾冠英街刘文彩公馆)里一幢三层小楼,楼顶一间大房子的四周窗户全用帘布封死,光线从屋顶亮瓦射下来,刘文彩让一群妓女在这里跳裸体舞。里面安有一张供10人并卧的大床,他同多名妓女同床而卧……对门有一家吕姓商人,全家47口,建有一幢三层楼房,站在三楼顶上,可以看到刘文彩房里的丑行…..。周东浩斗错了膀子。冠英街三层楼那个公馆是凌大住的公馆,对门住的不是吕姓商人,而是姓窦的军人。陈星奎先生祖屋在都长街,读小学以前住那里,与邻街的小孩熟,曾听“恒盛隆”吕家后人说过,吕家修在中山街的四层洋楼刚好对着刘文彩的“新公馆”,楼高于对面,看得见院内的活动,刘文彩让他们拆掉一层。上述资料表明,让对门楼房拆矮一层,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较大,只是发生的地点及吕氏洋楼究竟是三层还是四层楼不能确定。依笔者的判断,此事件发生在中山街“新公馆”的可能性大。只是,让对门楼拆矮一层的事件本身并不值得做大文章,因为刘文彩有可能将中山街“新公馆”作为办公机构,里面的活动不便显示于人;再说,即便是私人住宅,按传统风水学或风俗,彼的房势比己的高,置身于被人俯视或窥视的感觉总是不舒服的。权重川南的刘总办有这个要求恐怕对方哪怕是不情愿也会采纳。两家的疏通并达成协议的方式恐怕也比较理性。吕家也是有钱有势的大户,号名“恒盛隆”,吕家模、吕家斌、吕家元三兄弟开有经营黄包车的“大通车”行,“中正”镶牙馆,且信天主教。况且,没有任何因拆楼事件引起的不良纠纷传闻于世。有人却非要给别人栽脏一条是因为看得见里面“跳裸体舞”就是着意丑化了。不久前与几位老先生谈及这个话题,他们都一致认为刘文彩再怎麽奢靡也不可能在公馆里跳裸体舞,那个时代的人没得那麽开化。
刘文彩初来宜宾时,先住小北街的新盛旅社,不出两月接任叙府船捐局局长,随即迁至粮房街公馆。据有关资料描述:粮房街公馆极考究,整个大院是四进四套的院落,内院里是主人卧房,外院是仆从寝室。生活区、休闲区、娱乐区完全分开。主人卧房在北面,墙壁和地板都完全用约半米宽的松板修筑,层高约五米到五米五左右,卧房里还有一道暗墙,连接着一个封闭的石室。卧房前的檐坎约三米多宽,用一米见方约十厘米的青石铺成;坎边是二十厘米高三十厘米宽的凿花青条石砌筑;走下檐坎,一条一米多宽的石板路环绕着两株大铁树。再过去是一株银杏,银杏旁是葡萄架,紧靠着一棵倚墙的无花果树。走出这道墙的右面,就是刘文彩旳幕僚和秘书寝室,其修筑上与主人卧房不同,墙壁用青砖砌筑,外墙面的墙砖用炭黑调松脂涂成微微发黑的青色,砖缝用糯米浆调石灰浆勾缝,朩地板由很阔大旳树朩改制的整块板材铺就。主人卧房和仆从寝室的门扇倒还平常,窗户是花格窗户,而且嵌上了那年月比较奢侈旳花玻璃;屋面是小青瓦,屋脊上两条飞龙相向戏珠,屋擔由各种吉祥物装饰。秘书寝室的室內,墙壁用石灰砂浆抹面。层高约五米左右。仆从寝室在南面,修缮上就差了许多,墙面是石灰砂浆抺面的夹壁墙,地面是三合地,朩门窗,层高约2.8米,也是小青瓦屋面,只是屋顶上没有装饰。厨房在西面,东面是一排放置杂物的储藏间,其修缮和仆从寝室相同。进院穿过一条约两米宽的长长的石板路,石板用大约一平方米,厚約十厘米的青石板按一橫两竖的横竖错缝铺设。路的左侧是仆从寝室,右侧是幕僚寝室,中间就是一个大花台,花台过去有桑树、棕树、无花果等。从主人卧房再往里走还有另一个很开阔的院子,出囗通往一条狭小的巷道,据说专为战备留置,所以院內没有太多旳房舍,只有靠进门左手边旳一排小房间和对着门又背靠着主人居所旳一排警戒人员居室。这个院子里种了许多植物,有两株樱桃,一株枇杷、一株银杏、一株杉树、两株女真子树。在墙角处栽着一大丛泡泡花,成了小孩子们藏猫猫的好去处。——显然提供资料者曾常出没于斯。描述虽然细致,但公馆的总体轮廓交代得不大淸楚。该公馆后来扩修在南面增加了一个耳院,院门开在冠英街。耳院的西式门楼很气派,高于其他街房,青砖砌体,灰塑装饰,给川西,即安仁刘公馆的门楼相似,具有民国时代川西豪门宅第的风格。门额题有“丰沛旧家”,这四字在“文革”中已被涂抹。门楼左边约三米处的方石柱上刻有“刘氏墙界 民国十九年”,可能公馆扩修时间是1930年?冠英街大门无论是形式还是实际意义已取代了粮房街大门。刘元华还记得两院由一段长长的巷子连接。笔者于2009年8月26日上午特地去粮房街公馆遗址查看。粮房街已改建,新楼与旧房参差,已成为狭窄雍塞的菜市。刘氏公馆五开间一楼一底的门面还保存着,只是己面目全非,墙壁刷上一层厚厚的白灰浆,原来位于左边五分之二处的石朝门己拆除,大门移至正中,改为现代铁钎子门,给人终年紧锁,內己荒芜的感觉。八十有五的杨世炎老先生在该公馆隔壁住了多年,他热情地请来掌管大门的李国英老太太开锁进院,陪同笔者参观并讲解。说是该公馆“解放后”已几易其主,先后为宜宾县招待所、军分区敎导队、宜宾市交通局进驻。登上隔壁八楼楼顶俯瞰,刘公馆平面呈两个长方形(北院与南院)横向组合,占地约四五千平米。除了“北院”那排五开间一楼一底穿斗木质门面,(也谓之‘倒座’,已呈朽颓状)及“南院”的门楼,其余统统改建。市交通局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将其改建成多层砖混楼房供职工居住,近年另择新居迁出,该院己人去楼空,待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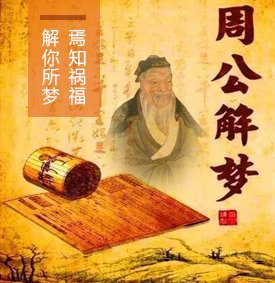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