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在宜宾开办了“新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禁烟应寓禁于征” 原叙联中教员黄藓青遗稿(1963年11月8日定稿)披露:刘文彩利用中央禁烟招牌,大量公开贩烟。早已特设了一个“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刘任总办,又在川南范围内重要地区特设了“某某区禁烟查缉处”,由所在地县长,或特派员任处长,还设“某某区禁烟查缉处分所”,设所长及职员若干。严密查拿“私犯烟禁”的无业游民,于是及时来一个“禁烟会议”。1927年夏季,堂哉皇哉地召开一次“川南禁烟会议”。会场设在中山街旧抚州馆内正殿,大门前扎有雄伟的柏枝牌坊,上嵌有八个金字:“川南禁烟会议会场”,派有武装士兵守卫,出入人员佩带出入证。会场中设一主席台,刘文彩为主席。主席台两旁,设两个速记员(黄藓青、赵石如)座位,其次设两个全场负责的主干人员座位(县长沈眉荪、商会会长刘蜀光),以下设若干席次,会议出席的县长、处长、所长,及其他人员,约为一百五十人左右。掌握全场及事前安排布置,多出自沈眉荪;刘蜀光只负责部分责任。鉴于刘文彩的威风,人们奉命唯谨,到会的人很整齐。会议的中心内容是:一,统一收购。禁烟查缉总处对烟土是统一收购。可分为:1,在云南迤西采办的上色货;2,从云、贵、屏山等处收购来的中路货;3,又从四川各地零星收购来的下色货;4,拿获没收来的各种不同的杂色货。总处拿来分别掺和,高高地制定价目,搭成分配给各区,再由各区分配给各分所,及小贩、吸烟户头。二,按期缴款。烟额货色既有分配,应缴款若干,不难一账算出:1,每区总共应缴款若干,首次先行缴款若干,其余的分若干期缴清,不得拖欠;2,按期赴总处领货,有加无减,办得好的,缴款时回扣加多,并规定惩奖条列,毫不通融。如和地方因“禁烟”发生严重纠纷,准各处自行酌量处理,上报备查。三,优定运费。运货,上缴货款,一切往返费用由各处长担负全责,准作正式报销。四,严拿“宵小”。认真严拿敢于触犯“禁令”的一般无业游民,或由别地偷运入境,私买私卖,以及假冒禁烟处名义,在外进行各种招摇活动,影响“禁令”的“宵小”,按照情节轻重,准由各级负责人便宜处理,或报请总处核办。……会议开了两天,虽有一点小争议,提案还是顺利通过了。闭幕时还摄了一张集体照,刘文彩又送与会者每人一张自己的放大照片,还附有上下题款。闭会后举行了盛大丰美的宴会。
宜宾县鸭池乡人刘玉山是宜宾最先涉入吗啡并将其打人入上海等地贩卖购回军火的商人。据宜宾资深文史研究专家朱大文遗稿披露:1929年后因覃筱楼下野到上海玩,向刘玉山透露刘文彩收的公土(生烟)堆积如山,销配有限等信息,刘玉山灵机一动,打起刘文彩的主意。刘玉山专程回宜宾拜见刘文彩,向他吹嘘上海有关烟土的行情。那一次仅送刘文彩爱妾凌君如的礼品就花了二千多元,其中在上海永安公司买的一串珍珠项链就耗去银元五百,绿玉戒指一只一百五十元,大衣料二百多元,还有象牙麻将及名贵摆设等;还送了刘文彩一部小轿车。据有关资料记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宜宾市正气巷即现人民银行址是一个名简国光吗啡商的住宅。简国光与刘玉山同乡,也是刘玉山的至亲。简除吗啡生意而外,在宜宾栈房街还有山货店。简胆小怕事,把吗啡作坊开在自己家里,规模很小,很隐秘。吗啡运往上海,由在上海中华路开百货店的侄儿简锡恩代售。刘玉山做中人,通过协商后,简国光把吗啡作坊转让给了刘文彩。刘玉山介绍一位名范少云(宜宾人,曾由刘玉山带去上海学制吗啡技术)给刘文彩。刘文彩便于1930年始,在这里开设吗啡厂。
没想到制造吗啡既容易,利润又比公土利大10倍以上,一担烟土制成吗啡只重百两左右,体积缩小也就节省了运费,也便于携带,销路也广。刘文彩疑心重,初始让范少云每天只搞几担试试,获利后才每天增至10担以上。刘玉山心贪,对刘文彩采用长线钓大魚的伎俩,开始几次售得的夲利全数汇给,刘文彩也贪得无厌,越搞越多,增加了刘玉山的压力;况且他在上海渐渐出名,要应付青帮及小瘪三,得花大量的金钱,自己得利不大,他便用消极限制的办法对付刘文彩,推说烟质不好,成色差,销路迟滞,同时将出售的货款交重庆驻军陈兰亭师长买吗啡到上海销售(陈兰亭时在重庆南岸弹子石设有吗啡制造厂),将刘文彩的钱握在手里作周转金;刘文彩催促时,推说货未出售,催得急时,多少汇一些应付,用这种藕断丝连的办法一拖就是一年多时间。这边呢,刘文彩追究范少云,说他制的吗啡有问题,要找內行査验,便去找帮覃筱楼制吗啡的陈技师及另两位重庆技师,试验后都说没问题,刘文彩才知受骗了,电告刘玉山回来结帐。这时的刘玉山巳将刘文彩的货款作夲翻了几滾,把欠款全数汇还给刘文彩。刘玉山在上海代刘文彩卖了吗啡,将其款代为刘文彩购买枪枝弹药,从中再赚取暴利。刘玉山当时从日夲人手中买手枪是一打12支220元大洋,而转卖给没有购买途径不知行情的刘文彩则为每支手枪大洋120元,多赚了他几倍的钱。刘文彩当时想成立一个手枪连。在上海购得枪械后,托英国轮船“万流”或法国兵舰“钢健”暗中运到重庆,到重庆后交刘玉山的驻重庆办亊处经浬林月明,再设法转运到宜宾。每次偷运枪械不少于2—3打,有时10打之多。
刘玉山在1932年刘文彩退离宜宾后才敢回来。范少云一直为刘文彩制造吗啡,直至1931年腊月才离开去了重庆。听说刘文彩退离宜宾时还存有不少吗啡。
有资料称:刘文彩在宜宾开办了“新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是崇庆州人张挽谰,文书是杨家骅,总务是罗吟苍,会计是王季旻。公司共买了四条轮船:一,“老蜀通”号,(由两条小轮船合并而成,马力最大——笔者注))经理叶宗元;二,“元通”号,经理周志勇;三,“南通”号,经理肖景伯;四,“昭通”号,经理陶伯宣。刘文彩撤离宜宾后,四艘轮船先后为21军潘文华及民生轮船公司所有。当时,“川南航务管理处”处长吴子愚与航运办事处负责人均为刘文彩心腹,故凡是由宜宾外运的烟箱和部分“个子货”(即“川土”)均由这四条“通”字号船接载。故其获利之厚,远超过宜宾其他公司轮船。从该公司成立,到1932年刘文彩败走,这四条船装运的鸦片数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从1928年到1931年这几年中,估计至少在一亿两上下。另外,还运出很多吗啡,再由重庆转运上海,这也是无法统计的。此外,杨森的“统一”号轮亦曾为刘文彩由宜运出烟土二十万两到汉口。
鸦片输入中国,始于十九世纪初叶,在前清嘉庆时代就有了,自两次鸦片战争后,门户洞开,外国鸦片逐渐由沿海深入内地各省。美国人吉尔门在他的《四川游记》中写到:“无论城市或乡村,凡被余询问者均称吸烟的人数占全人口百分之五十。”(《四川月报》1933年第三卷第五期)作为“烟城”的宜宾,吸烟者恐怕不在此数之下。当时几乎“任何人家,每有客来,必摆烟灯,以烟敬客,有似今天以纸烟待客一样。如果客来不摆烟灯,好象礼酒不设,待客之意不恭。”(《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8页)。鸦片垄断经营一直是刘文辉24军的摇钱树。说到烟祸,持罪者不只是刘文彩们,“……他们拖烟帮、抢地主,也都是我们批准的。说实话,当时我们没有钱,抢地主为什麽不可以?运鸦片换武器和钱,养活自己,打击敌人,为什麽不好?”(此文是樊光华根据马识途1984年8月23日在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工委召开的“解放战争时期成都籍田地区农民运动座谈会”上“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川康地区武装斗争的讲话”录音整理。)刘文彩们有理由,马识途们也有理由,贩烟吸烟者们都是有理由的,因而,那个时代的烟祸泛滥情况可以想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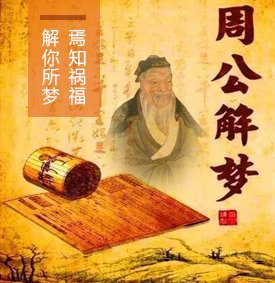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