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璋-为国保土察地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的铁蹄蹂躏我东北三省,南京的大街小巷,涌动着东北的入关难民,秦淮河畔飘荡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血泪歌声。作为地理学家的黄国璋,眼睁睁地看着野兽的铁蹄践踏着祖国母亲的胸膛,他的心快要碎了。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相反调集30万大军对工农红军进行围剿。黄国璋气愤、心痛,和师生们走上街头游行请愿,要求举国一致,枪口对外。而蒋介石的答复却是无情的镇压。黄国璋再次为报国无门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 山河破碎,国无宁日。长期霸占缅甸的英国,乘我东北多事,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调解之机,借口缅甸和我国云南西部的南北未定界悬案,攫取我国班洪银矿区,激起云南人民的极大愤慨,派代表团到南京向中央政府呼吁求援。当时我国边界地理不清,外交争执难有依据,须组织实地调查考察,绘制山川形势地图,确定两国边界。黄国璋得知此消息,对英帝罪行十分气愤。他慷慨激昂地说:“晚清时期的留学生,面对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侵凌,提出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而地不可失,种不可奴,国不可亡。如今日寇侵我东三省,英国又在云南边疆打我们的主意,真是欺人太甚。我是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只要国家用得着我,一定要发扬先辈爱国精神,共赴国难。”后经各方联系,决定由黄国璋教授负责筹组云南地理考察团入滇。黄国璋欣然应命。经多方努力,筹措法币2.4万元,购置从德国进口的先进仪器,与国际联盟派来的奥籍专家费师孟(H·V·WISSMANN)教授及滇籍外交专家张凤歧、助手王德基、严德一等5人组成考察团,经专业培训并筹足路费后,于1934年中秋出发。时蒋介石忙于“剿共”,交通阻塞,乃绕道香港、河内到达昆明。英国政府慌了手脚,忙派人到南京交涉,以阻挠考察团进入争议地区。蒋介石不敢得罪英国,与之订立中英两国政府关于暂缓两方人员进入争议地区考察的协议。刚到昆明的考察团得到的是任务被取消的消息。黄国璋眼看一腔热血,两年筹备好的计划付之东流而心急如焚。他以云南南部当时在中国地理学界尚为盲区为由,经与云南地方当局协商,改去西双版纳考察热带资源。11月,黄国璋率考察团顺迤南大道翻越海拔2000-3166米高的哀牢山脉,递降至1000米左右的普洱、思茅高原,下澜沧江边的卑湿低坝,勘查西双版纳全境。从迤南至允景洪共24个马站,仅两站通汽车,其余全靠马驮轿乘。他们晓行夜宿,边走边工作,沿途绘图摄影作笔记,并调查访问。黄国璋除抓全面外,还兼农林地理。时值旱季,“山径变为悬梯,无论骑乘,备感忐忑。”(《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4期)步履之难,难以想象。沿途常遇老虎、豹子、野象及毒蛇出没,须巧妙周旋,方可避害。路上的宿店有的隔三四十里,有的隔八九十里。晓行夜宿,必须赶店,否则夜宿林边,必遭野兽侵扰。普洱、思茅系滇南名城,考察团到此时,只见城内十室九空,街肆馆舍关门落锁;所见城乡居民,多是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大腹如鼓,脑壳如瓜,史称瘴气之乡,都因疟疾为灾。自元江以南,气候渐热,蚊蝇四季不绝,高原人士谈瘴色变。在昆明就听到“欲过元江坝,先把婆娘嫁”的警言。考察团一行,严格注意防蚊,可喜均未感染疟疾。元江河谷海拔仅500米,而周围都是2000米以上的高山,故气候酷热,考察团成员个个汗流浃背,彻夜难眠。黄国璋总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考察团绕西双版纳一周,考察滇缅、滇越边界,勘察了澜沧江河谷。搜集到的文字资料和图片都极其丰富珍贵。黄国璋用平板仪步测景洪坝曼景囊村前的田亩图,研究傣族土司的土地制度和灌溉系统。图成后明确傣族沿袭的土地制度,是土司有大片官田,居灌溉渠首,由百姓集体共耕,作为劳役。民间耕地为村有,居灌溉下游,由各村头人计户授田,各自耕种,收赋三成。公私田亩,图上分明,极似汉族古代的井田制。研究结果使黄国璋极为兴奋。他和张凤歧详细探讨这种制度形成的历史。他认为,不论怎么说,它都证明西双版纳和内地农业文化的血缘关系。黄国璋深知这样的考察机会难得,他要求团员们勤于采风问俗,广作社会调查,并为各族人民摄像,还购买许多少数民族服饰实物带回南京。考察历时半年。在总结这次考察时,黄国璋兴奋地说:“这次我们看到,这里的热带资源原封未动,面积有30万方里(即30万平方里),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英法帝国主义向远东掠夺缅甸、安南热带资源贪得无厌,犹觊觎这块宝地。我们这次经广东、广西、云南河口一带地区调查访问,华南沿海的雷州半岛、海南岛和广西的龙洲、滇南河口各地,栽培热带植物均难免冬季寒潮、夏秋台风的灾害。西双版纳因位在北回归线以南,热量充足又属印度洋西南季风范围,北有高原屏障寒潮,东南距海较远,可免台风袭击,是今后栽培热带植物的理想宝地。”
此次考察开学者考察西双版纳之先河。黄国璋著的《滇南人生与自然》、《滇南边疆局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资料翔实,描述生动,曾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引起各界极大兴趣,为解放后对这个地方的考察与开发起开拓性作用。考察团带回的图片实物,令学术界耳目一新,赞叹不已。民族学家凌纯声、马长寿等,认为这是一次全方位的考察,除地理农林学外,还丰富了民族学和社会科学,使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名扬中外。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国璋多次率队翻山越岭对川康、汉中盆地、嘉陵江流域、陕南进行考察。1938年率30多人的考察队,历6-12月的酷暑与严寒,步行或骑马翻越麻日雪山,拜会月孜土司和已故九世班禅大师肉身像,并给德钦汪母活佛摄影留念,观看藏民族天葬大礼。1958年,他身处逆境,以62岁高龄之躯,率陕西师大地理系师生到秦巴山区作考察。他著的《西康边防问题及解决途径》,其意义已超出单纯的地理学;他的《汉中地理志》被国家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为地理志的范本推广;《渭水河流域报告》《陕西经济地图》等,对陕西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黄国璋不怕艰苦,不辞辛劳,巍巍青山,滔滔江河,莽莽草原,皑皑雪域,到处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迹,他的这种实干求真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同事和莘莘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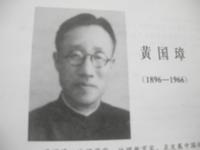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