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平生范吾俦——悼念江晓天同志
我们的朋友,我的兄长般的朋友江晓天同志走了。就在10月7日,重阳节的早上。他的老伴李茹送他去医院,走出门,在公寓电梯的轮椅上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
他走得很突然,但很从容。他在病中留下遗言:他走后,丧事从简,不要麻烦组织和亲友,让他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向远方。他嘱咐:把他的骨灰撒向大海,让他同女儿——1975年在南海舰队牺牲的烈士靳虹为伴。李茹平静地讲述着晓天的最后时光,让朋友们动容,肃然起敬。
晓天走了,甚至连骨灰都不留下。但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友谊。他的为人和为文,他一生淡泊名利,成为吾辈的典范。
今天的读者,包括文艺圈子里许多人,不认识江晓天,甚至不知道江晓天的名字。但是经历过上个世纪下半叶文坛风雨的人们,几乎都熟知江晓天,知道他作为一个出色的编辑家和评论家所作出的贡献。晓天1941年15岁参加革命,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历任小学教员、华中建设大学教育干事、《青年文化报》主编、《山东青年报》副总编。全国解放后,在团中央工作,后来出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他作为一个职业编辑、编辑室主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经他之手编辑和审批的许多书稿,成为红色文艺经典,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人们当会记得在读者中影响深远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这些长篇经典,都是经过江晓天之手,走向读者,走向全国,走向一代又一代人群的。晓天在做文艺编辑工作时,乐意扶持新人,全心全意地为他人做嫁衣裳。许多后来成为名人的作家,如茹志鹃、陈登科、鲁彦周等等的第一部作品,都是经江晓天的扶持而面世的。
江晓天很有见地,但大多数情况是“述而不作”。他对文艺创作有许多很好的见解,但却很少写文章,很少对作家、对文艺创作指手画脚。他常常为作家出主意,成为作家的“军师”。有人说,姚雪垠背后有一个“军师”,那就是江晓天。上世纪60年代,姚雪垠刚摘掉“右派”帽子,着手写作《李自成》。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政治氛围和社会氛围中,姚雪垠要出版大部头作品是有相当难度的。江晓天为姚雪垠出主意,要他写信给毛主席,汇报自己的创作计划。江晓天通过可靠渠道把信呈给毛主席,果然得到主席的批示。稍后,江晓天代表编辑部到武汉,把“最高指示”告诉姚雪垠,姚激动不已。姚雪垠在“文革”中避免了各种干扰,潜心创作,这里面有江晓天的一份功劳。此事已传为佳话。
江晓天具有文艺评论家的勇气和素养。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中央书记处任命为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兼文联研究室主任。他同冯牧同志一起,率领他们的团队——研究室的同志们一起奋斗。我记得有丁宁、刘锡诚、郑伯农、刘梦溪、李兴叶、李树声、丁道希等同志,为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披荆斩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当时在人民日报社工作,记得晓天率领的团队,常常为人民日报撰写“本报评论员”、“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批判“极左”思潮,扶植新生力量。我正是在那一段时期相识晓天,相知晓天,而成为莫逆之交的。
作为一个评论家,晓天对作家满腔热情。许多作家寄书给他,请他批评指正,请他写文章。他总是花许多时间去阅读作品,他读得很认真,很仔细,甚至对作品许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他对作家对作品提出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从不“大而化之”。他对作家充满热情。就在前几年,安徽作家鲁彦周邀他去参加研讨会,多年不出行的他,还是带着病体,同永旺同志等一起长途跋涉去安徽。他赴会是没有任何酬劳的,同时下“有偿评论”之风大相径庭。
晓天淡泊名利,但同文艺界的朋友,特别是评论界的朋友有着很真诚的友谊。自从光年、荒煤、冯牧、达成、洁民走了之后,晓天身体不佳,走不动了,但他仍然十分关心文艺,关心文艺界,关心评论。有时,我们在协和医院碰见,他总是问起文艺界朋友们的近况,问见过朱寨吗,他身体如何?问同上海有联系吗?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李子云情况如何?言谈中,吐露出他对朋友们的关切。去年秋天,北京评论界的部分老朋友,永旺、顾骧、锡诚、阎纲、丹晨、西来、秦晋和我等十余人到晓天家里探望,他十分高兴,带着病体,由李茹推着轮椅,陪我们去旁边的小饭馆吃饭。并且相约,到明年秋天再聚会。没有想到,就在大家期望相聚的日子,晓天静悄悄地走了。他生前有约,已难实现,我们只好到八宝山为他送行了。昨闻噩耗,作诗一首,送晓天远行:
晓色天光出徽州,江南热土少年游。
三红一创业绩在,淡泊平生范吾俦。
我们会来到他的身边,再道一声:晓天大哥走好,到天国那边去安息吧!
缪俊杰
2008-1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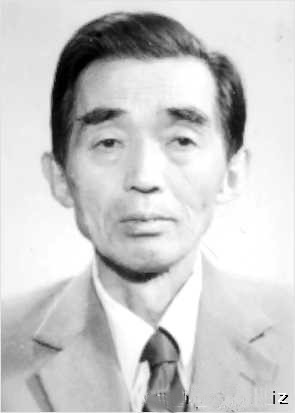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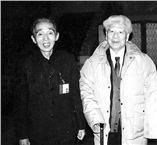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