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骄傲——我的老朋友江晓天
江晓天,这个被文艺界、出版界朋友们誉为“京城名编”的人,走完了他82年的一生,在重阳节(10月7日)的那天,本该相约去登高的,他却独自到天堂去了。他走得很平静,很安详,很从容。他的老伴李茹大姐在他去世的当天打电话来说:这两天他身体很虚弱,我就带他到医院去看医生,还没有走出电梯呢,他就在轮椅上睡着了。悄悄地,告别了人世。无疾而终,尽其天年。走得平静,无怨无悔。他留下的是一生清白、一世淡泊的美名。
大约在三四个月前,缪俊杰、顾骧、阎纲、谢永旺、陈丹晨、秦晋、何西来等,我们这帮子在20世纪80年代文艺评论界还算得上比较活跃、又与晓天知心的小老弟们,想念病中的老江了,牵挂久不见面的老江了,就相约着一块儿到老江的家里去看望他。于是,我们从偌大的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来到了位于望京小区的老江的新家。这是一座巍巍然的高层建筑,室内窗明几净,很适宜老年人居家养病。见我们来了,晓天坐在沙发上,精神很好,操着浓重的家乡淮南口音,嘘寒问暖,问这问那,仍然关注着文坛上的事情,倾听着思想界的动态,为熟悉的朋友取得的成绩高兴,为洁泯等一起并肩战斗过、不久前过世的朋友伤感。只是本来就弱不禁风的老江,愈加显得瘦弱了。我们不忍心让病中的他陪我们坐的时间太长,他毕竟在病中,怕累着他,就请他先到卧室里去休息,我们几个难得见面的老哥儿们继续神聊。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聊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不平凡的岁月,聊冯牧、丁宁以及老江他们于1976年组建的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聊1978年又如何在荒煤、冯牧与他合作的时代转为文联理论研究室,如何揭批“四人帮”及其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鼓吹和推动解放思想,重建文艺界,推动伤痕文学创作,等等。卧室里静静地,他像是睡着了。我站起身来,走到卧室的门口向里窥视,但见他正侧起耳朵来,听着从客厅里飘进来的每一句谈话。那天中午,在俊杰夫妇的安排下,我们一行和晓天、李茹一起到附近的一家饭店里用餐,吃的是西餐烤肉,晓天自始至终精神很好,食欲也不错,让我们这些小老弟们为他感到高兴。
过了不久,我又打电话向李茹大姐问老江的近况。她说,她和晓天都感冒了,发高烧,住了一次医院,刚出来没几天,现在情况比较稳定。我放心了。大家聚会的情景,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哪想到,晓天竟然这么快就离我们而去了!
对我来说,晓天亦师亦友。他虽是我的前辈和领导,但与他在一起,感到特别真诚、可亲、平易,一点儿也不用设防。他1941年参加革命后,就在我的家乡一带活动,在那里度过了战斗的青年时代。他告诉过我,他参加了1948年我家乡的潍县战役,而潍县战役是扭转华东战局的大战役。八路军攻克济南—青岛一线上的要冲——潍县,才给济南战役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潍县解放后,成立了潍坊特别市,第四天,晓天就参与创办了《新潍坊报》(《潍坊日报》前身)。今年4月28日,恰逢潍县战役胜利60周年,《潍坊日报》拿出60个版面作了历史回顾,家乡朋友给我寄来一大厚叠当天的报纸,我就想起了当年的报纸的开创者之一、年轻编辑记者江晓天。后来,他又担任过《山东青年报》的副总编辑。此后,他与出版和文艺结缘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编辑出版事业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室主任期间,主持和编辑了当代文学史上备受称道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以及《草原烽火》《烈火金刚》《刘胡兰小传》《董存瑞的故事》等多种优秀文学名著和青年读物。但凡在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曾经作为《李自成》第一卷责任编辑的江晓天,不仅帮助作者姚雪垠悉心打磨了那部名著,而且在“文革”后期,给处于苦闷和困境中的姚雪垠出主意,给毛主席上书,而毛主席的批示,促成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江晓天得知消息后,毅然乘飞机到武汉,赶在某出版社编辑的前头把《李自成》第二部的稿子拿到手,背回北京,从而促进了被“砸烂”、停止工作多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复社,也使许多编辑同事从干校回到了北京重操旧业,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一个有口皆碑的故事。稍后,要将此书翻译成外文,江晓天又被调到外文局所属的《中国文学》。文坛上得到江晓天的帮助、扶掖而成为知名作家者不在少数,如茹志鹃、鲁彦周、陈登科等,都不同程度地受惠于老江。“文革”中地下流传的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能出版,也得到过江晓天的支持。以我亲身经历的来说,如果没有江晓天的帮助,陈登科的《风雷》的出版,怕是没有那么顺利的,无怪乎鲁彦周生前在合肥举行的《陈登科文集》发行仪式上深情地说:“《风雷》的出版,江晓天下了很大功夫。”在其漫长的文艺编辑生涯中,他是一个称职的伯乐,他以自己无私的行动和辉煌的业绩,无意中为自己铸造了一个“京城名编”的荣誉称号。
“文革”结束后,他被任命为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领导小组成员,继而又担任了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后改任副秘书长)兼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参与指导了文艺界揭批“四人帮”阴谋文艺的斗争,他所主持的《文艺思想动态》影响和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时,我先后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和《文艺报》编辑部工作,特别是《文艺报》复刊初期,由于冯牧既是《文艺报》的主编、恢复文联和作协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又是文化部党组成员兼理论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后又兼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和书记处书记,一身几任,复刊后的《文艺报》没有片瓦之地,就借住在礼士胡同129号北院冯牧的办公室里,与南院里江晓天主持的理论研究室隔一条小胡同,许多选题的确定和许多重大动作的策划,几乎都与老江沟通商量,包括晓天在内的研究室的诸位同志,也常常是我们的常备作者。宣布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5个文艺家协会被解散10年后恢复工作的三届三次中国文联全委会、中国文艺史上划时代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主报告的起草工作,都有江晓天的汗水。他还肩负着向中央领导通报情况的任务,两次大会编印简报的繁重工作,也落到江晓天的头上。这些幕后的工作,大半不为人所知,他也从来不作炫耀。
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恢复工作后,万事俱兴,江晓天积极参与了许多方面的工作。那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还没有分家,他参与创建了作家出版社,兼任作家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作家柳萌来电告知,江晓天是作家出版社第一任总编辑,张僖是社长,他当年是编辑部主任。特此更正。——作者。2008年12月22日。)巴金就任中国作协主席,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周扬就任中国文联主席,提出创建“中国文艺资料馆”。江晓天受命具体抓文艺资料馆的筹建工作。他调集人马,很短时间内就把工作开展起来了。最值得一说的,是把许多旧日的馆藏珍本古籍都一 一加了蓝布封套。岂料周扬患病住进了医院,后继者又有了新的举措,放弃了周扬的筹建文艺资料馆的计划,于是,江晓天的努力功亏一篑。有一次,我到资料室借书时,在书库里看到,那些装进封套里的珍本古籍,躺在书架上,连书名都还没有来得及写上,不禁为老江一叹。1981年受中国作协委托,《文艺报》主持全国中篇小说评奖,晓天被聘为评委。继而,晓天被聘为第三、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初建,在周扬和荒煤同意与主持下,老出版家李庚组织了《中国新文艺大系》的组稿、编辑、出版,江晓天是这套书编委会的成员。这套大书选题的提出,是受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启发,从文学扩大到文艺其他领域。老江还具体承担了中篇小说集的编纂工作,并撰写了长篇《导言》。
江晓天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位忠实的同行者和有资格的见证者,也是一位有卓越见解和史识的评论家,尽管他写得不多。他的《文林察辨》和《江晓天近作》两个集子里,收录了他对新时期文学的观察与见解。作为《中国新文艺大系·中篇小说卷》导言的《新时期中篇小说的崛起》一文,大体可以看作他80年代写的文学评论的代表作。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到他卧病之时,他从来没有放下过编辑、审读和研究历史(包括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长篇历史小说研究一直是他的文学视野中的长项。自20世纪60年代责编《李自成》名声大振以来,虽然也编过许多革命战争题材、农村题材的小说和回忆录,但研究历史小说成了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每次见面或通电话,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总是回答说,受人之托在读一本什么历史小说。
我虽然无缘同晓天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在新时期文艺诸多问题上的观点,我们是非常一致的。从揭批“四人帮”在文艺上的余毒、同“极左”思潮的斗争,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兴起,我们经常一起合作,互相支持和鼓励。长期的编辑生涯养成了他勤于阅读和思考的习惯,他和他所领导的文联研究室的朋友们,随时关注着各地新出现的青年作者的创作,对八九十年代的文艺创作如数家珍,他也随时关注着文艺思潮的脉搏跳动。而正是由于当代文学评论和对当代文学的关注点上的一致,我们从相识、相知而成了挚友。他随时关心着我,把我当成可信赖的小兄弟。80年代中期,我奉调离开《文艺报》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此时,作为文联书记处书记的晓天,向中国文联党组和书记处提议,要我去文联理论研究室代替他的工作,并得到了同意。当我知道了晓天的苦心后,真是非常感动,尽管事情并没有实现,而我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想:知我者,晓天也。
晓天去了。文坛失去了一位著名的编辑家,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和挚友。晓天啊,您为人作嫁一生,您甘为人梯一生,您是当代文学编辑的骄傲!如今我的这些话,只能对着天堂说了。安息吧!
刘锡诚
2008年10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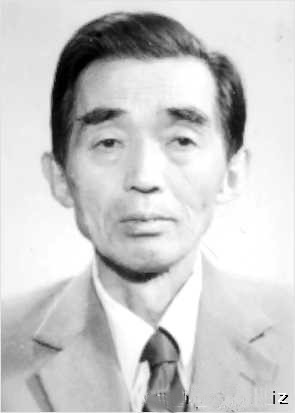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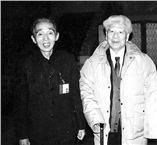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