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火旺——动乱年代跳槽的“燧人氏”
十年动乱,乌云漫天。陈火旺回到上海复旦,校领导和专家教授早已“靠边站”,或被批斗,或被关押;教室、实验室全部尘封,校园里高音喇叭鼓噪不休,造反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面对这种状况,满怀报国之志的陈火旺心在颤抖、在流血:世界上科技革命浪潮叠涌,西方发达国家已将计算机科技作为一种战略产业在加速发展、推进。而我国刚刚起步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竟被政治风暴摧折了。“天予不取,必受其殃;时至不收,必遭其咎”。中华民族难道又要倒退回到愚昧、落后、封闭、无知的洪荒地步吗?
铁匠后代的陈火旺因“根红苗正”,幸免成为造反派的靶子。他想起了一位伟人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便悄悄地找个僻静之处温习和钻研计算机理论。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纵使在十年“文革”大夜弥天之际,国防科研战线仍有少量院所在坚持重大项目的研究,当时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就是属于少数坚持科学攻关的单位之一。1967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华东计算机所负责人听说复旦大学新近从英国归来一位计算机软件专家,正是该所紧缺的人才,喜出望外。他们找到陈火旺提出邀请,一拍即合——陈火旺巴不得有一处施展身手的舞台。随后该所以“帮助锻炼改造”的堂皇理由借调,复旦大学“造反”派只好放行。这样,陈火旺跳出了“停课闹革命”的是非之地。
到华东计算机研究所,陈火旺就发现,当时国内计算机软件还处在拓荒阶段:布满“010101”的专用纸带就是计算机程序软件,这种纸带断裂后,工作人员就用剪刀、浆糊将其修补粘接好,还用香烟去烧孔。原始的“钻木取火”式的技术,鞭策着陈火旺奋起直追的使命感。在大街上贴满“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标语的氛围中,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用将近两年时间主持设计了我国计算机软件领域第一个符号宏汇编器,并成功地应用于“655”计算机上。他提出的递归结构式的符号宏指令产生技术,也相继被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上海计算机研究所等单位采用。
蹉跎岁月进入七十年代,原哈军工计算机专家慈云桂为组建远望号测量船专用计算机攻关队伍到沪上“招兵买马”,通过内线找到了陈火旺。陈火旺得知这是国家重点工程。二话没说就答应“跳槽”——反正慈云桂能包办一切调动手续,连陈火旺那分居10年的妻子吴明霞也被他从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调来了。
时值“哈军工”南迁长沙,学院百废待兴。研制计算机的工作点,安置在郊区一座破烂的农校养鸭棚里。地上积满了20多厘米厚的鸭粪,墙上涂着“砸烂狗头”一类的标语……这环境,跟当年居里夫人熬炼沥青渣的破旧漏雨棚相差无几。
条件差,改变它!陈火旺和众多专家教授们一起,持锹挑担,清除了鸭棚的积粪;用白灰浆刷净墙上的污言秽语;没有电,自己接线安装。家眷搬来了,没有宿舍,把教室用三合板隔成几个小家。一盏灯瞧着几家人,一婴哭饿,全队闻声不安。当地蛇多,夜里下班回家怕踩着,手中拿一根竹杆或树枝,像避躲挂弦地雷一样,边拨拉边走。
苦中有乐,陈火旺劲头十足,他终于登上了为国争光的大舞台。在慈云桂教授推荐下,国防科委指派他主持和领导国内第一个Fortran编译程序会战,负责编译器的总体设计,并于1974年完成了441B-Ⅲ的Fortran编译系统(该成果在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3年至1978年,陈火旺肩负起远望号测量船中心计算机DJ151语言系统的研制重任。除1975年被硬性要求派往湘西农村支援农业学大寨,其余4载春夏秋冬,他作为符号宏汇编系统(MPL)和Fortran编译系统设计师,尽可能瞄准当时能了解到的国际先进水平,设计了MPL和Fortran编译器的全部框图,提出了因子分解式全局优化技术,使目标码运行效率大为提高,成为国内第一个具备全局优化的编译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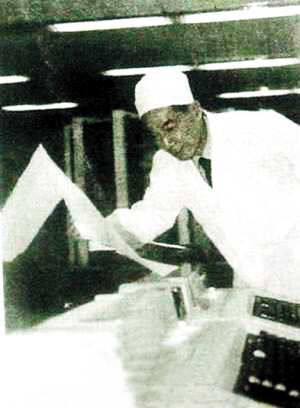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