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军
每当我看见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校服,背着崭新的书包,系着红领巾高高兴兴地向学校走去;每当我看到那些年轻的男女骑着摩托车,开着小车,打着手机,哼着流行小调在马路上兜来兜去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发出一阵阵的感叹:"多好啊!孩子们,你们能生活在今天是多么的幸福啊!"那无限的感慨就不断地涌上心头.
我属小龙,从小父亲就给我腊月二十五过生日。
就这样过啊,过啊,一直过了几十年以后,有一年的一天,我在县城里开会,每个人都填一张个人简历表。表填好以后,县里的一个干部看了看却很认真地对我说:“啊呀!老王,你这个人命好,毛主席属小龙你也属小龙,他老人家是二十五日的生日,你是二十六日的生日,刚差一天。咳!你没听人家说过吗,腊月小龙头,不是帝王也是侯”。
我不很经意这位干部的相命说。可是到了后来去韶山瞻仰毛主席的旧居时,却不知道为什么找了一位韶山老人问起毛主席的生日,究竟是公历的十二月二十六日、还是旧历的腊月二十六?不知是湖南老乡没听懂我的话,还是我没听懂他的话。他只是一个劲的在嚷:“么子吆?龙历、龙历”。
湖南老乡讲的什么意思我没闹清楚,坐上从韶山回家的火车,心里却有点洋洋得意、飘飘然了。迷糊着眼睛就想开心思了:嗯,也许还会有那么一天,要应了城里那位相命干部的那一说,说不准哪一天时来运转,我还真要有个王公侯爵的当当,唉,管它呢!那一年我已经五十七岁了,家境才刚见好转,就美得想了这么多,真是的,现在想起来觉得真有点好笑。
又过了好几年,一直到我六十多岁以后。我的一位婶婶才对我说:“你是正月初一的生日,正月的蛇不好,命太硬,所以才给你改成腊月二十五过生日”。我想了想,本地是有忌讳“正蛇二鼠三月牛”这一说,怪不得城里那位相命干部的话一直不显灵,这正月和腊月就差远了么。差就让它差去吧,什么命不命的,好活歹活我也一辈子了。一辈子,哎呸!我那叫什么样的一辈子呀!
我小的时候,和现在可不一样,那还叫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纷乱的社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经常在开仗,伪村公所的人不断地来家里摊粮派款,各种苛捐杂税压在人民头上,老百姓连腰也伸不直。
我的祖上不知哪一辈也许还有些本事,置买了很大的一所院落,还给我的爷爷起了一个良贵的名字,就是到了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也是秉仁义礼智信叫着。听起来是很有些文化。
到了我有记忆的时候,家境已经衰败下来。几经拍卖,原来的一所大院也变成一个小院子了。
父亲、三叔和我三个人就生活在这祖上留下的三间破烂房子的小院里。院里的一切都是破旧倒塌的,院门、院墙、厕所没有一样是完整的。只有一棵不大的槐树长的却很精神。经常还招来几只喜鹊“喳、喳”地叫上几声,都说喜鹊叫是好事到,可是一连叫了好多年家境还是不见好转。三叔这人心眼好,脾气也不赖,经常指着槐树对我说:“侄儿,你就快些长吧,等你长到树杈这么高,三叔教你赶马车,咱们父子也好翻翻身。”
村里有个小学,我只上了几天,家里就没钱供我再上了,我也不爱上.每天就跟着一帮杀猪宰羊的屠户给人家帮忙,挣上一顿饭,啃上几块骨头,有时遇上个好主,还能给家里拿点下水,就这样过着。
到我十七岁那年,进城在一家杂货店当了跑堂的小伙计,干了三个月,没给开一文钱。
“龙生龙,凤生凤,斑鸠养的谷谷种”。杂货店的老掌柜是个吝啬鬼,他那十几岁的儿子也是个守财奴,到第四个月下来,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没给我一分钱。他们父子俩还给我解释:跑堂的小伙计就是赶口磨衣裳,意思就是只管我吃饭,其它就什么也不管了。
赶口磨衣裳?说了你们的话啦?原来答应的一个月还给我一升小米子也是赶口磨衣裳?一怒之下,我跑到新南堡村拉上我的好朋友福儿进城,把那个小财东打了一顿,气是出了,小米子没要上,饭碗子也堕了。堕就堕去吧,反正我也不准备做跑堂的这营生了。
半年后,又到汾阳县的北关园给人家织土布,这些土财主一个比一个难侍候,也没干多长时间就又跑了回来。
村里的三、五个年轻人是经常凑到一块天南海北地胡侃神拍,我的这几个朋友中有的叫木头塞塞、神拍六日、雀(QIAO)日,还有的叫石塌天。一天,他们说起到太原当兵不错,吃的、穿的都很牛气。说话的时候谁也不在意,可到我耳朵里就动了心,过了三、五天,我没有对他们说,就一个人步跑着要去太原当兵,走洪善、祁县到太谷后住在一家车马店,碰巧遇到我们一个村里的几个在太原做买卖的好心人,他们对我说:“啊呀!孩儿,太原的兵要往外地开,一开出去就不知道牛年马年才能回来,要当兵可不敢去太原当啊!”
我听了这几位老乡的话,第二天,就和他们一起相跟着返回了家,重新操起旧业,就这样又一年过去了。
第二年,日本人就侵占了太原,那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的十一月,日本人沿同蒲铁路线直下,榆次、太谷、祁县日本人是不战而得。
到这一年的十一月九日,日本军队川岸师团石井四郎的部队就开始攻打平遥,国民党驻扎在平遥的中央军是高桂滋的部队,虽然他们做了坚决的抵抗,但终究因为增援无望,坚持了三个月,也就是一九三八年的正月十四,日本兵炸塌了平遥城上东门南段的城墙,平遥城也丢失了。
第二天就是正月十五,传统的元宵节。平遥城里再也不是向过去那样的红火。只有三五只纸糊的灯笼,在这寒冷的冬天露出一点幽暗的烛光,任凭西北风呼呼地吹打着。糊在灯笼上的红纱也被这寒风撕破,发出咝、咝的声音,仿佛在向人们倾诉着这痛苦和不幸。日本兵把进攻平遥受到阻挠的恼怒、仇恨一起洒向无辜的平民百姓,侵入了平遥的日本兵疯狂地在城郊附近烧杀抢掠,对上东门附近的居民更是施行了血腥屠杀。
我们村附近有个村子叫候郭。受日本兵的欺负更是厉害。候郭村有个侯老汉多年来一直在兰州一带做皮毛生意,听说很是赚了几个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竟敢带着两个妻侄女,兴冲冲地跑回老家来过个年。
侯郭村里住满了日本兵,老汉回到村里后一看这架势不好,就把两个妻侄女安顿在喂牲口的草棚里,每听见门外有响动,就把草堆扒开,让俩女孩钻进去。有意躲避日本兵的骚扰。
这一天,侯老汉又小心翼翼的将谷草盖好,一转身,一群日本兵象鬼一样地蹑手蹑脚地过来了。日本兵看到穿戴整齐的侯老汉在草棚前发抖,走过去劈劈就是两个耳光,口里叽哩咕噜骂了几句,顺手夺走侯老汉的金镏子、玉石烟埚后,本来转身就要走。这时,躲进草堆的俩个妻侄女憋得实在是喘不上气来,想露出头来透透风,这一露头不要紧,恰给日本人看见,老汉一着急,就发楞怔。片刻,要想让俩孩子再躲进去已经来不及了。侯老汉就要用自己的身子遮挡孩子,突然,野蛮的日本兵就开枪了,侯老汉挣了一挣,捂着胸口前的一大滩血躺下再也起不来了。两个姑娘被疯狂的日本兵从草堆里抓起来拖走了……
平遥县城丢失,那些过去威风凛凛的县太爷,此刻也不知到逃到哪儿去了?城里城外整天是鸡犬不宁,人哭马叫。南门外、阎良庄等村庄的父老乡亲、妇女儿童不断地遭受枪杀,这座素以商贾名扬天下的古城霎时狼烟四起、人心慌慌。
这一件件、一桩桩受欺侮、遭凌辱的事不断传进我的耳朵。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国破家完、民族危亡这些大道理,但是仇恨日本侵略者无辜杀害父老乡亲、欺男霸女、抢劫财物的心理非常强烈。
我的家乡南政,在平遥县城北五里。旧军占据县城时就经常到村里来骚扰,日本人一来,把我本来就很贫穷的家庭变的更加困难了。我们父子三人尽管每天使气卖力的受着,可家里还是那老样子。这个窝囊罪哪一天才能算熬到头呢?
那一年我已经不算小了,经常听人们说:文水的云周西村附近有共产党、八路军,于是这年春天的三月初一,邻近的五里庄正在赶庙会唱戏,二十岁的我就和村里的三丁日、福儿三个人一起拿定主意,徒步向北行了二十多里,到宋家堡要过汾河投奔八路。
这年是个虎年,正月打的春。三月的汾河结冰早已消了,但是找遍附近不见一条渡船。那是盘踞在文水城里的敌人怕人们私渡,沿河都收走了。几十里的河道,只有一两个渡口,盘查的还很严。
三丁日年龄大几岁,心眼也多:“要再找不到船,我就不去了,啊!”三个人沿着汾河找船走到王家庄村后时,他果然就返回去了。福儿问我说还走不走?我说由你。于是倆人又走到宋家堡。太阳已经落山了。
我的姑姑就在这个村里,姑姑知道我一天没有吃饭,也知道我想当兵的心事,赶紧张罗着做东西给我们吃。姑夫却搭拉着个脸一句话也不说。家乡里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姨夫、姑夫、舅舅的老婆,是不亲的三个亲戚。那是有些道理的。姑姑在这里唠唠叨叨地打劝着要我住下,哪儿也不要去,明天就跟着你姑夫种地去。姑夫他却低着头是一声也不啃。吧达吧达地抽着他的旱烟,抽上几口就没火了,装上、点着继续再抽。头也不抬,眼也不斜,正眼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姑姑疼我是个没娘的孩子。可又没办法收留我,匆忙中在村里请来一个半神,说要给我算命,那神汉拉着我的手,左相右看了好半天才说:“这孩子有难,出路在北”。他用红纸给我们每人画了一个阴阳五行八褂图,要我们收好,还对我倆说七七四十九天不敢丢了。
许多年以后我还能记得那个神汉,也常常想起他,也许他是真的有灵,也许是看破了我的心事,也许还是个地下共产党。
不管怎样,总算给姑姑宽了点心。她哭着给了我们几个玉茭面窝窝,踮着小脚送我们到村口。还是不停地在哭,她哭我也哭,都说离别时是有千言万语的嘱托,可她却哭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姑姑还是没有说一句话,一句也没有。她哭着、走着、走着、哭着回家去了。
夜、更黑了,天、更冷了。我挽起了裤腿,就要渡河,还不到河心,浑身就冻得哆嗦开了,牙禁不住的要打,身上禁不住的在抖,那个冷呀,真是厉害。真有点招架不住。
汾河两岸没有人守候,一晚上只过来一队巡逻岗哨。沿汾河渡口横拉着一根粗蔴绳,那是摆渡的梢公做缆绳使用的。我们俩就抓住这根缆绳,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淌过这快要淹没到脖子上冰凉的河水。
越走越深、越走越冷,欲返也不能。两个人互相拉扯着上了对岸,浑身上下都冻成硬梆梆地,抖一抖冰漓碴还直响,不远处有个村庄,好不容易才找到个人家给开了门,人家一见我们这两个怪物,是高低不让进门。给了个火,俩人在野外搂了一堆茅柴点着,烟熏火燎了半天,那一夜,总算没冻死。
到了后半夜,在文水县的门世村找到了八路军的一个武装队,队长姓苗,方山县人。他安排了五、六个人七审八审的审问了我们半天,问我们是哪个村里的?认得张三某人不?这张三某人长的有多高?什么样子?这人在村里干些什么?他们还担心我们是坏人派来的探子,天快亮时,才给了一老碗米汤和两个黑面馒头,吃的真香,吃完饭就换了衣服。从此就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活,这是一支由八路军晋绥抗日根据地工卫旅派出的武装,全队约有一百多人。
兵就这样当了,至于我走以后家里还发生过其它什么事情没有,那我就不管它了。
六十年之后,在三丁日晚年的时候,他一个人经常在家里呆呆地坐着。我有时过去看看他,还买过几次豆腐干、饼干一类的食品和他一块吃吃。闲聊起来,他说了几件事,使我深受感动。
他说我们当兵走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听人家说,头天晚上在汾河滩里打死了两个偷渡过河的人,直把他吓的快要死了。硬是撑着胆子过去看了看不是我们,他才放了心。回到村里,就悄悄地告诉了我父亲,结果是叫我父亲好一顿臭骂,头上还挨了一刮。
父亲是属于老实巴交的那种老农民,在村东种着二亩西瓜,想来这人走败运时是“马倒连鞍转,嘴眼一起歪”。那一年因为我当兵出走家里本来就不平静,可巧就在那时候有个偷吃西瓜的人被父亲抓住打了几下。打的正上火,父亲又问那偷瓜的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偷瓜的禁不住打只好照实说:“花堡则的,叫阎锡山”。
你说这个偷瓜的人也是,他叫什么名字不好,偏偏他就和山西省行政长官阎锡山的名字一样。父亲顺口就说了句:“阎锡山?你以为说成阎锡山祖爷们就不敢打你了?告给你,我打的就是你阎锡山”。
这句话,既不是针对阎长官,也不存在什么政治意识,纯粹是一种巧合。谁会想到这偷西瓜的小子还有点头脑,挺会钻空子。他挨打后就一赌气跑到村公所,将父亲说“打的就是你阎锡山”这句话添油加醋地报告了伪村公所的几个人。
伪村公所的人本来就对我父亲没好感,一直在怀疑他的儿子跑出去是当了八路军的兵,二罪归一,不问清红皂白就罚了父亲三百斤西瓜,还算是给了面子。
忠厚实在的父亲啊!你可知道,阎锡山是什么人?那是你能随便打的人吗?你看看偷西瓜的这小子损不损?
三丁日他还对我说,伪村公所也找过他的麻烦,怀疑是他把我送到八路军队伍里去了,他硬是没有说,人家可把他捣砸美了,饿了一天还冻了一晚上。多亏王家庄有个亲戚来出面担保,才把他放了回来。
真是的,这个中国革命呀,牵动着多少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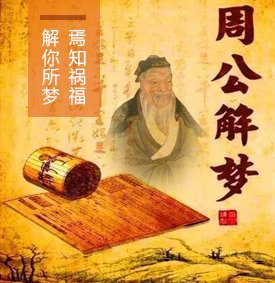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