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首次行动
这年秋天的一天,我们驻地从吕梁山里来了工卫旅的一个团,说是要到祁县益晋公司抢夺一些布匹,给八路军做今年的冬装。要我们武装队配合。
吃过晚饭,可能也就是九点来钟,我们就向祁县出发了,从文水县的南胡家堡到祁县县城也就是二十来里。那天夜里特别黑,路旁长满了高梁。战士们排着队,一路上静悄悄地,只听见嗖嗖的脚步声。不多一会儿,就到了祁县的城北,看见益晋布厂的围墙已经扒开了一个口子。这时候队伍好象有些乱,厂里没有电,黑呼呼的。
不知道是不是被布厂方面发现,我听到还打了几枪。不时地传来几声乱七八糟的叫唤声,因为领导没有安排准备战斗的命令,所以,一切都是按原来布置的进行。
这次抢布战斗很成功,好象没有牺牲一个人,就缴获了大量的布匹,解决了部队以后几年的服装供应问题。我虽然仅仅是个新兵,但也能感觉到这是一场里应外合的战斗。总感觉到布厂内有自己人在配合我们的行动。
一个当兵的,领导安排干啥就是干啥,不必多问。来扛布就是扛布,我进了仓库搬起布匹扛着扭头就走。
祁县到文水的南胡家堡路上,马车拉的,推车推的,肩膀扛的,人流不断。少说也有两三千人。
武装队的炊事员也来了,平遥县长寿村人。身大力不亏,他一个人就扛着足有十匹洋布。从山里来的部队领导还表扬了他,要我们向他学习,说:“你们看这个同志,他那扛了有多少?大伙都要向这个同志学习,多扛几匹布,今年冬天就有棉衣穿了”。
就是这个刚受到表扬的炊事员,人家胆子也大,半夜路过长寿村时,居然把十匹洋布全放到老乡家里给他藏了,出来不知又从那个车上搬了几匹,回去就交了差。只有我跟他相跟着,就我们两个人知道,他要我给他保密,我做到了。几十年守口如瓶。
以后部队进山时,他也进山了。在又一次偷卖连队的咸盐时,技术上出了问题,露馅了,似乎是没有怎么处理他,把他撵走就算了。
再后来我退伍回地方后,在平遥街上还碰到过他一次,他称我是老战友,在城里西街上的一个国营饭店设宴招待了我。他一面喝着酒,一面向别人吹嘘:“我们都是三八式老八路”、“提着脑袋闹革命来的人”、“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
他以为我还不知道是我们部队把他撵走的。拍着胸膛对我说他后来在日本宪兵队给日本人做饭,是做地下工作的。他还说:“那一年冒着生命危险在日本宪兵队偷了一支手枪和十发子弹,给咱们部队送去,哼!他们才给了我一担小米则,真他娘的不够意思。咱们就不给他干啦”。
就因为这用枪和子弹换来的那一担小米,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从汾阳西山顾了个牲口驮着小米往回走,到汾河渡口时,小米让人家抢了,被日本人收买了的便衣汉奸特务说他私通八路,绑上往城里宪兵队送他,多亏那小子还机灵一不留神才跑脱。
他跟饭店的人很熟悉,两只脚踩在櫈子上,借着酒疯,海阔天空地瞎吹着,吹的是天花乱坠,说的是有板有眼。连那饭店的大师傅也跟着称道他,指着他对小服务员说:“看见了吧,那边坐的那两个人,过去都是八路军,那要不是没文化,嗐!现在都到中央当大官了,还能坐在咱们这小饭馆吃饭?”
我耳朵听着他在吹牛,表面上却瞎应付着,心里是亮堂的多了:笑话!你这也叫提着脑袋闹革命?你是一天到晚在想着法子偷东西,走到哪你就偷到哪。共产党的你敢偷、国民党的你敢偷、日本人的你也敢偷,就不怕日本人把你逮住死拉死拉地?
他说的很快,我的嘴巴子总是赶不上他,跟着瞎哼、哼。他还问我现在干什么,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又羡慕地对我说:“人家你闹对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革命了一场”。
隔了一会他又埋怨我说那次偷布如果能鳔住的话,咱们两个人拉上一马车,只要咱们不说,谁也不会知道。那一晚上咱们就成了财主了。
真是胆大妄为,恶习未改。
天快亮的时候,工卫旅的部队就撤回山里。又过了几天,由我们武装队掩护,靠当地的老百姓把这些布匹运往山里。途经文水开栅镇时,武装队先将开栅镇包围,以应付特殊情况的发生。
这里我想说几句与本书无关的另一件事:
一九九零年春天,山西文水县发生了一起制造和贩卖假酒致死人命的大案,时年,我那位当过炊事员的老战友已经快七十岁了,在祁文公路上开着一个小饭馆,和他儿子一块经营着,凑乎还可以过去。不知怎么把他也牵扯进去了。据说,他也倒卖了一些假酒,数量不是很多,没有直接毒死人命,可也受到一个多月的拘役、审查。还罚了不少款,究竟是怎么会事,我没有细问过。
反正,我觉得他这人本事是有一点,脑瓜子也会算计,可就是靠不住,算来算去净做些算住自己的事。
刚入伍我们部队主要就活动在文水县的云周西村一带。说是武装队,实际上是为山里的八路军扩军征兵的一个办事机构,我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催公粮、宣传抗日,还要管抽大烟和老汉打老婆的事。
记得我们在操场操练立正、稍息、齐步走的时候,屁股后面总跟着云周西村的一群小孩,他们扛着木头棒子、红缨枪,在模仿着大人的样子。就叫儿童团吧,我想,后来成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女英雄刘胡兰也肯定在那些儿童团里。那一年她大概也就是七、八岁吧。
一九三八冬天,武装队因人少就主动撤进山里,训练了一个来月,计划还要回到平川活动,但随着敌人的兵力增加,给武装队的单独活动带来很多困难,这样,我们这支武装就奉命在交城的西社村正式编入了八路军工卫旅。
最初,我好象是被分配到二十一团,几营几连?我可记不清了。我们那个连长大概是叫孙一奇,营长就不知道是谁了。反正我是当战士。
正式编入工卫旅后的事间不长,我们就在汾阳的一条公路两旁和日本人打了一仗。这也是我当兵后正二八经地打的第一战。
晚上,我第一次参战,跟着那些老兵往前走时,已经能听到汾阳罗城方向打枪的声音,说实话,心里多少还有些紧张。现在可和在云周西村那会当兵不一样了,是刀对刀、枪对枪的真打。
那一天我们的大部队在打汾阳罗城,让我们埋伏在公路两旁,打从汾阳出来增援罗城的敌人。在夜幕渐渐降临时,我们兵分两路,神不知鬼不觉地迂回到张花村。我们设埋伏的那个地方好象是个三叉路口,南北一条是汾阳到文水的大路,朝西还有一条进山的小路。
人们眼睛睁的大大地,连大气也不敢出,就静悄悄地等着,战士们间隔距离不过二尺,福儿就在我身边,当兵以后,部队有规定,一律改称大名,他叫陈树福。他用脚轻轻地踢我,凑近耳朵问我:“怎么样,怕不怕?”我心跳的加快,分明是紧张,口里却不愿意说出来。硬着头皮撑出:“不怕”!
潜伏了一晚上,鬼子没有行动,天快亮时。我们以为就没戏了,人们开始有些麻痹,揉揉眼睛,伸伸胳膊舒舒腰,妈的,好困!白折腾了一晚上。就在这时,汾阳的敌人乘车出动了,模模糊糊地没法数,可能有二百多吧,鬼子们一心想的是増援罗城,压根就没想到我们敢在这个时候,在他们占据的县城附近设置埋伏,一个心眼就知道往前赶,看着鬼子越来越近,我们觉得时机已到,各种火力一起开火,可把那些兔崽子们给打美了。
出发打仗前,看见老兵们用的都是“六五”式步枪,羡慕的就不行。我和陈树福每人都给了一条旧枪,大概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七九”烂板枪,有枪没子弹的“晋阳”造,打一枪压一颗子弹,还算不错,有的战士只有几颗手榴弹,这一仗打下来,其它的不说,我怎么也的装备装备。
打伏击战就是这样,三下五去二,解决了问题就赶快撤。因为这里距离汾阳县城太近,北面还有个任洋村也驻扎着日本鬼子,万一他们两头增兵夹攻我们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的首长在喊叫着:“撤!”我盘算着,撤?不行。就这样撤?那我不是白忙乎一晚上了吗?我的捞点便宜,这便宜就在眼前呀!垂手可得。我对陈树福说:“看见了没有,那边土圪塄下那几个死鬼手里肯定有枪,你给我看着点,我去拢过狗的来”。还没等他答话,我已经猫腰跳了过去,爬到死人身上摘了两支步枪,低着头还想取子弹,陈树福也过来了,说北面的敌人过来了,他口里催着我快走,手却也在摸鬼子身上的子弹。
没打死的那些鬼子已经组织反击我们,一个老兵厉声地叫喊我们的名字,让赶快撤,日本人的枪打起来“咯儿、咯儿”的还有音乐,子弹在我们头顶上乱飞,幸好没有碰着。
等我们追上撤退的部队时,一个首长说:“你们两个这样可不行啊!我喊叫了半天叫撤,你们不撤,大家都在掩护你们,快走!”又赶了一段,大伙都觉得到了安全的地方,才顺了口气,坐下歇息。
前后左右看了看,有了新枪的不止我们两个,还有三、四个人也有了。刚才批评我们的那位首长,过来看了看我们的枪,说是好枪,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干部,那一天,听说我们的一个营长负了伤。他可能是营里的个副营长吧。他说缴获的两条枪给你们两个留一条,另一条归三班使用。
给就给吧,没有办法。
我们缴获的那两支枪是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枪膛上带着铁盖,颜色有点发蓝,拉一拉枪栓,“嚓啦嚓啦”地直响。好听也很好看。从那一天开始,我和陈树福就轮流背着它,那感觉就可以和我们今天骑着摩托车和骑自行车的人相比,就是不一样。那一仗我们打的不错,少说敌人也死了有百二八十个。
以后,我曾细细的想过这个问题,打仗这事情,不论是新兵老兵,临战前都免不了有些紧张。等到双方接了火真的打上了,反而倒不觉得怕了,看到我们还有几个战士负了伤,那就更火了。
一个当兵的,第一仗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打胜了,勇气、胆量就增加。打败了,也许就草鸡、稀松、吓破胆。
出发前,陈树福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块红布条条让我悄悄地装上,别啃声。什么意思?我心里清楚。枪子那玩艺可是不长眼啊!
在罗城路上打增援的这场战斗中,我们也伤亡了十几个战友。和我一起在云周西村参加过训练,来之介休县北贾村的一个青年,头一次参战不幸就负伤,头部和臀部都带着伤,流着血,在撤离战场抬着他返回的途中光荣牺牲了。按照领导的吩咐,在一个山坡上掏了个洞埋葬了他,身下只垫的块木板。
一场大战刚刚结束,我们部队正急急忙忙地往山里撤,领导决定留下我们三几个人做善后处理。我们几个人对于打仗死人这类事情都没有经历过,埋葬他以后,只是在山坡的土壁上划了个符号,写了几个字,前后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匆匆往深山里追赶大部队了。
这件事过去二十年多年以后,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的一天,有三、四个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突然来到我工作的单位,一进门就“扑嗵、扑嗵”地全给我跪下,声泪俱下地对我哭诉着,说他们是介休北贾村人,是罗城战斗中牺牲了的我那位战友的亲属,想清楚一下亲人牺牲的经过,还想要找到烈士遗体埋葬的具体地方。
我那个办公室本来就很小,他们这么一跪更挤得满满的。他们这一跪一哭,我眼里的泪水也是忍不住“哗、哗”地就往外流,赶快扶他们起来,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竭尽所知的一些情况给他们说了,比三比四地给他们说那个战友埋葬的情况。但是怎么也给他们说不清楚那位战友埋葬的具体地方。
那一仗,我们是从文水县的深山赶到张花村打埋伏的,我只能估计我们从深山里走了有二、三十里路,战斗结束后,是不是原路返回我都记不清了,那位战友就埋葬在我们返回的路上,大约有十来里地的一个山坡上。当年在土坡上做的文字记号,经过这二十多年的风吹雨打和人为的变迁,肯定是早就无影无踪了。
一个二十来岁的新兵,我根本就说不清楚我们是从哪儿出发的?途中路经哪些地方?叫什么村庄?山上到处都是坡,我怎么能记得把他埋葬在哪个坡上呢?
我对死者的亲人深表歉意,并为此而深深感到愧对战友。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打听到我参加了掩埋那位烈士的?烈士的亲属带着忧伤、带着失望、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走了。
也许从那个时期开始、或者说从更早他们就已经踏上了一条寻找亲人遗体的路程,几经周折,纵然使出浑身的解数,科学的、传统的、迷信的各种各样的办法都用尽,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二年,尽管是希望渺茫。这些忠厚善良的后代,仍然不畏疲倦、不屈不挠地寻找着烈士的遗体。
他们还断断续续地来找过我几次,我为他们的精神所折服,和他们一起去过一趟,再一次经历了那莽莽吕梁山。然而,带来的只有是更多的破费和瞎忙碌。还去哪儿再找呢?记不清是哪一位先人说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褁尸还?”这样的一句话,是呀!历经世代沧桑,中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哪一块土地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个年代里,为了祖国解放而英勇奋斗,他们没有模范和功臣的称号,甚至于连名字都来不及记下来,就悄悄地倒下的无名英雄,又何止成千上万呢?
介休北贾村我的这位战友就是这其中的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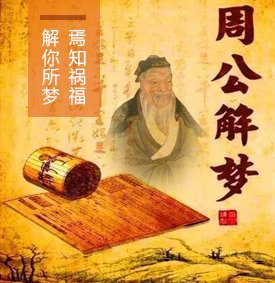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