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攻打草庄头
进入一九四三年,我跟着傅连长到团部侦察通讯连。他当连长,我到侦察排,排长是孝义人郝怀文。这一段时间不是很长。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和另外俩名侦察兵外出侦察回到驻地麻会镇后,老乡告诉我们:“你们的部队从后山沟里开走了”。
因为不知道部队去向,我决定当晚先住下等天亮再说。谁知道第二天天刚亮,村里又来了一些队伍,说是决死四纵队的一个连,为首的一位姓肖。当他听说村里还有二十一团的几个人时,便叫通讯员把我叫去。我向他说明我是二十一团侦察连的侦察班长时,肖说:“二十一团估计是向岚县方向去了,你们对这一带情况熟悉,就不要走了,先跟我们一起干吧”
肖有三十多岁吧,个头不算高,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是个什么样的领导,我吱唔着
他见我踌躇不定,又继续说:“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没关系,你们啥也别担心,咱们就在一块先干着,等找到二十一团时你们愿意走再走么,好吧?”
我揣度着这个人官很大,战士们都叫他肖政委,看样子他能主了事,就答应了下来。在他的直接指挥下,我经常外出侦察一些情况。此人好象有爱吃鸡的嗜好,而且最爱吃鸡头。每次我下山执行侦察任务时,他总给我几个钱让捎只鸡回来。
这个连也就是一百多号人,是肖政委的警卫连。很快我们就混熟了。他有一个贴身警卫是清徐人,我问过他,肖政委叫什么名字,他好象是说是叫肖克。是清徐、太原区的政委。
全国解放后,我见过肖克上将的照片,不像是他。我还翻过许多资料,都没找到关于这个人的记载,决死四纵队只有肖新槐任民运部长一说,而文化部还有位肖望东部长的曾用名也叫肖克。我没有什么特殊的事非要找领导不行,所以至今也不知道这位肖政委究竟是谁?
有一次,肖政委安排我往七区区委送信,那天下着大雨,我找到七区区委时已经浑身淋湿。为了烘干衣服,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沿着沟里往回走时,山洪暴发,把我冲走。也不知道洪水把我卷了有多远,神志还清楚的时候,一块巨石把我给拦住,真的是共产党的福分高,连我这个普通一兵都沾光呀!我连忙爬了上去才留下这条命。
那天为了早点赶回去给肖政委送情报,打了个早起就上路,没顾得上吃饭。走了半天,又和洪水搏斗了一阵,肚里灌了一肚混浊的泥水,呕吐了好长时间,嘴里还是泥沙满满的,饿的我前心贴着后心,身上是没有半点力气。
我半躺半卧在山坡上,浑身上下碰破的、擦破的、流血的、红肿的、青的、紫的是一块一块。疼的我睡是睡不着,走是走不动。半睁半闭着眼睛想呀想呀:这回怕是真完了,这前不见村、后不见店,深山老林的。才半下午,天就阴得黑乎乎地,这鬼天气鬼地方,谁还敢来?
唉!王树呀王树,这革命到底、革命到底。你这革命就这么到底了?刚才没有叫洪水淹死,现在怕是困也要把你困死,这一下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我这里正发着愁,忽然远处传来一声:“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也没啦坐过那好车马”的秧歌声,歌声由远而近。一个匝着腰带的红脸老汉骑着一头毛驴、牵着一匹大红马过来了。
他好象没有注意到我,还在扯开嗓子地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我可不敢让这救命的机会错过,赶紧就先跟老汉打招呼。那一刻也不知到咋地就来了一丝灵感,信口就编了句:“老汉,你这牲口卖不卖?”
真正是巧极了,他就是卖牲口的。他说刚才在前头村里就要卖,可是没有说对价钱。我说我是给部队买马的,你跟我到部队拿钱吧。还没等他答应,我边说边就要爬上马背,那匹马很有灵性,它好像知道我受了伤不容易爬到它背上去,居然前肢弯曲,双膝盖跪下放低它的脊背让我上,很奇怪,那老汉并没有吆喝它。就是觉得有些惹怪,一匹马么,它怎么就那么灵呢?这件事,后来我不知给多少人说过多少遍。说句迷信话,我真的怀疑是上帝有意安排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匹红马四只蹄子皮毛是白色的,以后的许多年,不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是遇到这种颜色的马,我都要多看几眼,看看它是不是救了我命的那匹马。
等我回去报信时,肖政委他们已经等急了,我把路遇的险情说了,又给了他信。肖政委边看信边从衣服堆里拖了件衣服让我快换上,顺口说了一句“此人命大”。也就算是表扬了吧。
他们几个又抱歉又感激地打发了卖牲口的那位红脸老汉。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卖牲口的红脸老人啊!我,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将会永远记得您,永远怀念着您!也永远感谢您!
草庄头是交城山里比较大的一个村子,地处交通要道。这里驻着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和一个警备队。主要用来封锁我方出入山区的人员和物资流通。敌人妄想以此来卡死我们。
不知道肖政委他们用什么办法收买了这里警备队的队长,约定好要在八月十七夜里攻打草庄头。这些情况,驻草庄头的敌人也好象有觉察。他们在八月十三、十四就从清徐城里运输了两天食品、弹药以防万一。
八月十七夜,我们先安排了民兵和各村的干部,让他们随后牵着毛驴来草庄头,我们就先出发了。
草庄头村外山头上,山神庙旁敌人修的那个碉堡很高。我们到了那里,在警备队长的配合下,肖政委先让四纵队的两个队员把日本鬼子的倆个哨兵活捉了过来。部队就一拥而上冲进了院子。那警备队长指点东房,意思是告诉我们东房里住的就是日本鬼子。我们就往东房里扔手榴弹。一阵爆炸声后,警备队的那些人早举着手出来了。等我们冲进东房一看,妈的!十几个日本鬼子全都被炸血肉横飞。墙壁、脚底、顶尘上全是血和肉皮,沾得满满的。
紧接着就让警备队的人集合,就在肖政委给警备队的人讲话的时候。突然,从刚才炸死日本鬼子的东房里跑出一名日本兵,他用被子裹住身体,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朝门外跑。我们几个先是楞了一楞,马上就反映过来:“站住,缴枪不杀,再跑就打死你!”
门外一条深沟,他竟直地就跳了下去。不用看,肯定摔死了。
这个日本兵跳下去究竟是死是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一九九九年夏天,也就是我去陈台村的那一次,特意驱车绕道草庄头。
草庄头村村头,坐着一群闲聊天的老汉,经他们仰面一指,我才知道当年被我们攻占的那个据点,是修在一个很高的山头上。奇怪!当时我怎么感觉它没有那么高呢?
大老远地来一趟也不容易,想的是要亲眼看看这自己战斗过的战场,现在瞧瞧那老高的山头,算了!
山神庙依然还在,和一位差不多年令的李老汉谈起,证实了那个日本兵当时摔下去就没气了。
但李老汉知道我是当年参加那场战斗二十一团的人时,他激动地告诉我,那时候鬼子强迫他在那个据点里给敌人做饭,那一天他也是忙了一晚上,给我们搬过战利品,还分到一袋洋面。他还说看见我还面熟,他还告诉我,去年他们村里来了一个日本人,就是我们当年俘虏的那名日本兵,活的还挺阔。
我,我想起了那位从崖上跳下去的日本兵,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很是同情他:你呀你!为什么要跑呢?假如你当初当了我的俘虏,今天不也是一位中日友好的使者了吗?
唉!这人世间,说不清,道不明……
这次战斗,仅仅几十分种,打死了十几个日本鬼子,俘虏了两名日本兵和一个警备队,彻底拔掉了敌人的一个据点,缴获了日本人的许多枪支弹药和食品给养,把这些东西分别由老乡运走,我们点了一把火,烧了日本鬼子的这个据点,我们就迅速离开草庄头。
在那个年头里,就没有安生过一天,有时候几乎是每天在打仗,甚至于一天就打好几次。
在清徐县的赵家山附近,我们还袭击过一次敌人。敌人退走赵家山方向,肖政委对我说:“王树,你们去前面看看,看看敌人是不是真的走了?”
我和汾阳的一名侦察兵到前面一看,敌人真的走了。我对汾阳的那名侦察兵说:“你去报告肖政委,就说敌人已经退走了。我呢?我再到前边去看看”。自己一个人就向前走去。
请读者暂且记住这位汾阳藉的侦察兵,有关他的情况后面我还要做祥细的交代.
我走到赵家山的一座庙后,踮起脚探起头向庙里张望。不料,庙里正好有退下来的日本鬼子,有两个戴钢盔的鬼子发现我在东张西望,连枪也不拿就从墙上朝我扑来。我一见不好扭头就跑,背后不知从哪又冒出一个日本兵来,他双手就要抱我,那时候我们穿衣服都不穿袖子,我使劲一把甩开。敌人仅得了一件外衣就又继续追来。所幸的是,他们三个人因为着急抓我都有没来得及拿枪。我用的是两头都锯短了的六五式步枪,调头就打了两枪。又拼命地朝前跑。
跟日本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交道,可有时你就是弄不懂他。刚才还有三个鬼子在追我,这会扭头看时,仅留下一个鬼子了。见我打枪,他也不怕,连躲也不躲,还在使劲地追我,好象非要抓到活的不行。
我边跑边前后左右扫了一眼,确实就是他一个人,我就胆正了。紧三步、慢三步地和他周旋着,好象是在打架,不是在打仗。他口里哇哇地叫唤着,脸色涨的象猪肝一样红,一指头指着我咬牙切齿地,做着要狠狠卡死的样子。我不会日语,用一口地道的平遥话骂他:“畜牲!惹你外祖宗的,你过来,祖爷们非跺死你狗日的不行!”
看来,日本人不一定是人人都聪明,也有傻瓜。眼前这就是个傻大个。已经远离赵家山有一里多地了,他还敢追我。
这个时分,我估计肖政委他们也快来了,就干脆蹲下,两眼一吊线就给了他一枪,就一枪,打了他一个狗吃屎,只见他前后挣扎了几下,倒在地上打了个滚,不动了。
我走过去踢了狗日的两脚:“你妈的,起来!你不是要卡死你祖爷么?”他使劲地翻了翻白眼皮,连着哼、哼了几声,就快没气了。正好,汾阳的那个侦察兵领着肖政委他们来了。
不知是谁挑头说了句:“挖个圪洞埋了狗日的”。有两三个战士就挖开了,刚挖了几下,几个人抬起那家伙就往坑里扔,他个头大,坑挖的太小,放不下。还想再挖几下,赵家山那边已经有鬼子过来了。
我们急中生智,给他背下垫了几个手榴弹,又把拉线套在他手上,仰面朝天放在坑里,我们就躲在老远的一个山坡上等着看他们的戏了。有三、四个鬼子过来,大概是找他,走到那死鬼跟前,摸摸鼻子看看眼,就要抬他。听说日本人有规定,打仗死了的人要抬回去。刚一抬,手榴弹就爆炸了,几个鬼子全完蛋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引来了赵家山方向更多的敌人,我们也就撤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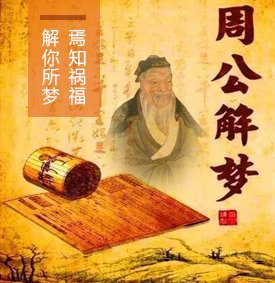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