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一)
母亲出身于北方书香门弟的大家庭,家里表哥表姐众多几乎都是大学毕业、各有所成。他们在学习或工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父亲和母亲的帮助指点,从 小就像一家人一样。每逢节假日或出差来北京时都会到家里来。从小我就听他们亲热地称父亲:二姑夫。小时候,看父亲和他们天南地北神彩飞扬地聊天,是一种享 受,而有时偷听父亲细声细语地同他们谈学习,谈工作,谈理想,评论社会也是一种乐趣。我常听表兄们私下议论:最佩服二姑夫了!我也常想,父亲的口才是一流 的。
一次,母亲带回家一个清瘦的青年,我看他一脸萎靡,和父亲三个人在里屋谈了许久,出来时都一副神淸气爽的样子。母亲留他吃饭,饭桌上大家谈笑风声。那人一再说:“我听老严的,听老严的。”
那时年少好奇,缠着问母亲才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抗日女英雄的遗子,因为出入中南海的亲戚家感受到社会的不平等,而写下类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 “反诗”,几乎被打成反革命。母亲尽全力保护了他,看到他因精神受刺激举止反常,母亲让身为医疗专家的我的二表哥给他医治,让父亲帮他打开心结。他谁的话 也听不进,却对父亲心服口服。(文革动乱中有造反派別有用心,颠倒黑白地说母亲迫害烈士子弟某某某,想要置母亲于死地。幸有学校正直人士,冒死揭开真相, 才得以死里逃生。这是后话。)
父亲待人隨和亲切,从不以势压人。讲起道理来,深入浅出头头是道,从哲学的角度讲,还多少有些诡辩的才干,几下子把你绕在里边无言以对。
小时候总覚得父母偏心,不喜欢我。一天吃晚饭时我忍耐不住抗议了:“你们偏心!”捧着飯碗,我环顧父母,历数事实。
飯桌上沉寂了几秒,父亲不温不火很和蔼地说:“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嘛,你哥哥是老大,开始我们只有他一个,所以习惯了。你妹妹最小,当然事事要多照顾多些,你自然就有些偏心的感觉了。”
几句话让十岁的我无言以对,从此就认可了。可見父亲诡辩能力之强。
父亲温和亲切,总是以礼待人,随和善良。在宿舍楼遇到打扫卫生的工人有时他会让到家里来请他喝杯茶聊几句,下班回来看到大院里的孩子在玩,他也会过去逗逗他们。
院子里经常有一群小孩在玩“跳房子”。(因为年龄相差较多,我从来就觉得她们是"小屁孩儿",不屑与之为伍)有一次,我从家里的窗户看到父亲下班回来, 走过她们身边居然兴致勃勃地也跳几下,引得孩子们拍手欢笑。大院里的孩子们都亲热地叫他:严大爷,从不生分地用官衔称呼他。
文革初,打扫楼道卫生的老郭中风摔伤入院,造反派们觉得让当权者去医院陪床照顾无儿无女的老郭是最好的惩罚。我知道父亲不会干活儿,但他一定耐心周 道,真情实意。外面造反派在闹腾,医院里老郭瘫在病床上已不能讲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好人谁是歹人,只能拉着父亲的手不停地流泪。父亲则非常温和地安慰 他,帮助他。
文革中父亲的表现也许是胆小懦弱的。他追随领袖,走革命路线,亦或也要自保,护家。也曾表态要和一些人甚至当时已被打倒的母亲划清界线。在许多人看来,他不像母亲那样坚韧不拨,宁拆不弯。但是我知道他是无奈的,而且是绝对有底线的。
文革初始他正在上海巿委负责“四清”工作,一个急电把他和搭档叶林召回北京。一下火车,一群乌合之众蜂拥而上,把叶林按倒并扣上亊先做好的大帽子。叶林当时 眼泪就下来了,父亲还算清醒,只是叫着老战友年青时的名字:“德茂!不要哭!”(后来叶林又被派去北大工作组,遭遇御用造反干将,为此人人皆知,更 加倒霉,这又是后话)
父亲在文革中沒有被完全打倒,而是被挂起来靠边站了。
有一段时间家里总有一群一群的人破门而入,他们软硬兼施,或是倾心交流,或是拍桌怒吼。我总是静静地坐在吃饭的外间伸耳去听,只觉得不管软硬,父亲都是一 个声调,不温不火而且像是嘟嘟囔囔地回应他们。我知道那是一些社会团体和大学的造反队,想逼他表态支持他们。我实在不耐其烦,私下里也想:或许父亲听从领 袖召唤,支持小将造反,站在一派,家里的状况会有改善。
有一天, 人群散去后我忍不住说:“爸,你就站出来吧。”
话音未落,他十分坚定的说:“不能站!坚决不能站!你小孩子懂什么!”
《工人日报》当时是国家的笫二大报,他的印刷系统据说比第一大报《人民日报》还要先进,造反派们看中了这个,想逼尚未被打倒的父亲站队。一来利用报纸做宣传,二来可以把印刷厂拿过去。或者即使不站队,也让他们使用印刷厂。
报社当时被迫停刊,做为一社之首的父亲在腥风血雨的冲击下站立不穏,但他心里太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了。即使是红太阳揮手,他也不往前走!在他柔弱几近窝囊的外表下,有着明智的理念。他推三阻四,大打太极,咬紧牙关。既不站什么队,也不让报社沦为他用。
历史证实他是正确的,那些曾经表态支持什么造反派的干部,后来多被卷入动乱的旋窝中。或被冠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桂冠",或被打成“五一六”份子。有成黑 手的,有成黑后台的。有的今天还在台上和某些造反派一起振臂三呼万岁,明天又被另一些人、或上头的什么人一句话而打翻在地,踏上千万支脚了。
文革后,父亲虽被某中央领导戏称为"髙级泥瓦匠"但该领导不由又加上一句:"是个好同志"。
也许父亲有大智却缺少大勇,但在那个“领袖一挥手,群众山呼海唤扑上”的年代,能保持大智者实在也算是凤毛麟角了。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如履薄冰,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他忠于红太阳,却绝不陷身群众斗争中。他明哲保身,不为别人两肋插刀,但也绝不整人。他嘴上十分革命激进,但心里的底线划在哪里只有自己知道了。他正直清廉两袖清风,从不以权谋私。被人称为:“老好人”。
我是被迫下乡的。
那时,伟大领袖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父亲在飯桌上说:“有 出息的青年应该到农村去。"
”你有出息,你去!"我立刻顶了回去。我可不想去。
父亲一声沒吭,只是黙黙地吃饭。
現在想想,那时父亲也并不想让这个嘴硬而缺少生活能力的女儿去乡下。但是他也需要口头革命,需要听从领袖教诲。
母亲的学校有人写匿名信给我们学校的工宣队,说走资派某某的女儿应该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几年后在批林彪时,看到他的"五七一计划"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不免有些心相应。
我准备去山西插队,父亲拿出些钱让我去买箱子准备行装。我从小不知穷滋味,兴髙彩烈地去了繁华的王府井。在百货大楼对面的一个老店舖,一个老店员拿出个小皮箱说:"这是猪皮的,不太好。"
"那什么的好?"我问。
"当然是牛皮的。"
"有吗?"
"沒有。"
"那就是它吧。"
提着缝制尚精良的皮箱回到家,心里还多少有些兴奋。父亲看到,沒说什么,仿佛是轻轻叹了口气。可能是想:真是半傻不傻。
二十年后,这个皮箱又伴我去了美国。
父亲送我去了火車站。車快开了,我站在同学的背后从窗口向下张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看见父亲神色憔悴地呆站在那里。他瘦多了,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寒风中他只是眼巴巴地看着我,面无表情,始终一言未发,连手都沒能抬一下。
那一刻,父亲心中一定是翻江倒海。
母亲还在继造反派后,軍宣队、工宣队私设的监狱中煎熬。妹妹尚年幼。哥哥远在河南。唯一在动乱中能帮他顶一顶的我,又要”发配“山西。此一去山高水远,不 知未来。车开了,周围一片哭声,我泪眼模糊地向他招手,只见他身影渐渐变小远去,車一转弯就看不見了......
父亲去世一年后,我在梦里见到了他。这也是多年后至今唯一的一次。
我淸楚地记得:他微笑着向我走来,我高兴极了!沒有一点他曾经离去的感觉,和以往在家里一样。
他走近我说:”我要走了。”
"別走!"我急忙说。
"那好吧,我再呆一会儿。"他依然是那么柔和,不急不慢。
我坐在椅子上拉着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手臂上,真切地感受着他肌肤的温暖和弹性。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哽咽。我对自己说:別哭,别让爸觉得我难过!但我还是忍不住抽泣着哭起来,我紧紧地抱着他的手臂越哭越厉害......
于是,我醒了.醒来满脸是泪。我狠狠地擦去脸上的泪,真想抽自己:你为什么要哭!爸爸不见了!我不由地哭出声来。
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我清楚父亲确实走了!而这亲人离去的痛,深深地栽在了我的心中。
有人说,生命是轮回的。做这种梦意味着又再世为人,重托生了。
我不知真假,但我愿父亲和母亲从天堂重回人间,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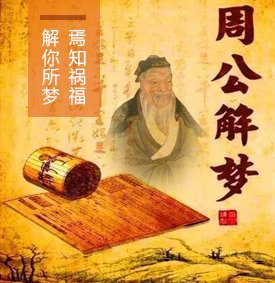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