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虻个人经历
个人履历
198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毕业,毕业时被分央视《东方时空》原总制片—陈虻到航天工业部团委,1985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在《人物树林》、《观察与思考》栏目做记者。1993年7月加盟《东方时空》,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1996年获全国十佳制片人。1997年组织召开了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2001年初赶美参加伯克利大学“媒体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2001年1月,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2001年10月主管《东方时空》,并兼任该栏目总制片人。在多年的电视新闻工作中,陈虻的创作经历,十分丰富,收获颇多。
工作经历
大学毕业时,陈虻被分到了航天工业部团委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了中央电视台,从小到大一直朦朦胧胧的“搞文”的念头在那个瞬间突然清晰起来。作为制片人的陈虻说过这样的话:“创作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创作的过程又是十分具体的。所以,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同时需要两种极具反差性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 陈虻在中央电视台的头三年里,没有具体的工作,如果说他干的事儿算是工作的话,那个工作就叫“打杂”。接收陈虻的人要不是当初看中他的人,他的工科背景让领导有些不情陈虻愿。三年里,每次报选题,到了陈虻这儿都会自动地跳过去。从陈虻上班的那天起,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谁在外面拍片子磁带不够了,一个电话回来,陈虻就扛几箱带子,买张站台票给送过去。谁的钱不够了,陈虻就负责跑邮局寄钱。谁要是外出拍片子,说:“陈虻,跟我走一趟。”这是三年里他觉得最幸福的事儿。“走一趟”对那个人来说是搬东西,联系车票,找住处都不用愁了,对陈虻来说却是学习业务的大好机会……陈虻就是这样成为《东方时空》总制片人的。 1993年6月的一天,当时《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孙玉胜靠着窗台对陈虻说,来《东方时空》吧。陈虻回家后看了20多天的《东方时空》,也想了20多天。“有两点理由,我决定来了,一是《东方时空》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儿干,我不愿闲着;二是《生活空间》当时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而从那个夏天开始,《生活空间》也渐渐成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1年11月5日,新改版的《东方时空》播出了。25天前,总制片人陈虻才接到改版通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一个天天要播的名牌栏目动手术,难度可想而知。陈虻戏称为:“就像一家饭店,一边营业一边搞装修。”身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还同时领导着《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这两个重头栏目。
人物生平
陈虻,生于1961年8月30日,2008年12月24日逝世。享年47岁。著名电视陈虻人,生前曾任央视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观察与思考》做记者。 198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毕业,毕业时被分到航天工业部团委,1985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在《人物树林》、《观察与思考》栏目做记者。1993年7月加盟《东方时空》,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1996年获全国十佳制片人。1997年组织召开了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2001年初赶美参加伯克利大学“媒体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2001年1月,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2001年10月主管《东方时空》,并兼任该栏目总制片人。在多年的电视新闻工作中,陈虻的创作经历,十分丰富,收获颇多. 网络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片子《分家在十月》,是我曾供职的央视新闻评论部的兄弟们攒的,已经成为中国电视史上最具智慧的黑色幽默作品。这个片子还有一个名字叫《陈虻诺夫回忆录》。在片中,时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白发苍苍。但是现实中,陈虻没有活到那个年纪,昨夜,他因胃癌去世,享年47岁。 陈虻喜欢穿牛仔裤,长发飘飘。才情丰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锐,情怀深沉。熟谙主流话语不乏叛逆精神。在我心中,这是最有理由享受理想生活的那种人,应该在城市边缘弄个诗意的居所,调素琴阅金经,饮茶读书,高朋满座,一不称意便可明日散发弄扁舟。可惜这样的生活往往属于那些满脸横肉铜臭逼人的房地产暴发户。陈虻,不过是电视与官场的双重压力艰难负重的中年男。 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想办法拖一拖,避开他的锋芒。他目光太敏锐,语言太精妙,那时,能做出个好片子与陈虻英雄惜英雄,曾是我很大的创作动力。《巴金》、《余光中》、《孙志刚》,少数几个自己尚能过关的片子都曾经过他的法眼。他可算是台里少数审片专注的领导,之后的点评,更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只是在场听的人常常只有一两个人。如今想来,十分可惜。他不仅指点具体的剪接拍摄采访技巧,也善于提炼深厚的人生哲理。有些话,在离开多年后依然感觉振聋发聩,比如他曾经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看完《社会纪录》,再之前是《纪事》,再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陈虻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连线》。印象中我的最后一次审片,签完字后他没有走,而是长叹一声,说:文飞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现在,也老了。我拿着播出单,转过身去,收拾台子上的带子、关机,眼中怆然泪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我离开了让我老得很快的编辑台和新闻评论部。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能量太多,多到可以分给很多人,我也曾幸运地分得一杯羹,这杯羹,现在还在滋养我。肉身有它自己的天命。但是,一个人的智慧,被许多人悄悄地拥有着,这样的价值,不与肉身等长。所以,此刻,我和很多人一样悄然叹息,但想到他将生命能量发散后,在地母黑暗而温暖的拥抱中开始深长的休息,我又感觉到一种平静的温暖。虽然从此以后,无论我拿出什么作品,都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去惶恐面对。 24日凌晨0:30,北京肿瘤医院,抢救黯然结束,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副主任(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 陈虻 因胃癌去世,享年47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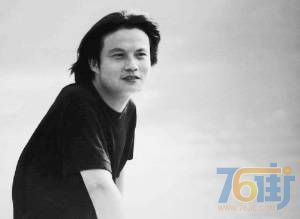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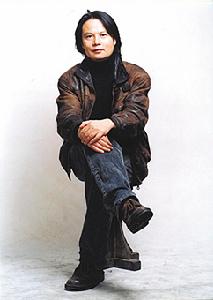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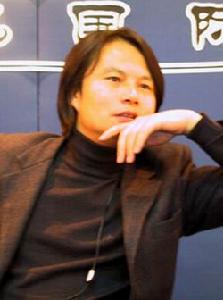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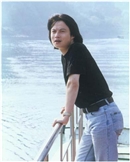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