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痕——再忆父亲
父亲没有读过书,从来没有进过孔夫子门。然而,他的账目却记得很工整、清楚,他的算盘也打得很精准。父亲年轻时在街上富先生家打工,一字不识。富先生是个很开明、很有学问的人,他的颜书写得特别漂亮,在古县渡那一带可是首屈一指。因为父亲为人诚实、本分,做事吃苦、勤快,所以富先生对父亲很看得起。富先生记账,就让父亲跟在旁边看着学。父亲亲身体会到,我们石门楼人因为贫穷念不起书不识字,在一起纠纷当中就因为一个字而失去了一口水塘,父亲把这一宗冤屈埋在心中,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学一些字、算,不要再吃哑巴亏”。有了这个机会,父亲很用功,早晚勤学苦练,一边学习打算盘,一边学习写字记账,加上富先生的指点,很快就能单独算账、记账,后几年,富先生的屠店全盘托付父亲管理。解放初那几年,父亲和泉生叔合伙开屠,我经常到屠店玩,看着父亲一边卖肉一边亲手记账,毛笔小楷字写得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是整齐、干净、清秀,有时我也好奇地翻开账本看一看,白纸黑字,写得那么工工整整。字是竖着写的,上面是赊账人的姓名,有的人的姓名上面还写着是哪个村;接下来是买肉的数量,几斤几两;再就是当日的肉价钱,当时的肉价钱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甚至是一天一个价;再下面写着“计币”两个字,“计”字最后那一竖拖得很长,那个“币”字藏在“计”字里面,写得很小,“币”字下面就是赊账的实际数目,“x仟x佰”依着“计”字那长长的一竖写着。那几年人民币是以“万、仟、佰”为单位,1955年以后才改为“元、角、分”。数目字都是大写的“壹、贰、叁、肆、伍、陸、柒、捌、玖”。已经还了账的,用毛笔顶端蘸着红印章油在名字上印上一个红圆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调理分明,一目了然。没有一笔一划涂改,没有一点一滴污迹,干干净净,比我的作业本整洁多了。看着父亲的账本,有谁会相信父亲是一个没进过孔夫子门的人?
大概是在我读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给我一本书,叫我一定要背熟,我一看,是一本《百家姓》,我不解的问:“背这个做什么?”“背熟这个有用啊!”父亲说,“背熟了这个,以后记账就不会写错人家的姓哪!”我接过来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读书又不用读这个”。父亲当即背了起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我听着父亲那一字一顿,有板有眼,很有韵味的声音,顿时勾起了我的好奇,我翻开书一句一句往下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书,四字一句,把那些毫无关联的字揉在一起,搭配得那么吻合,读起来很顺口,很有韵味,看着看着,当我看到“乌焦巴弓”一句时,忍不住笑了起来:“乌焦巴弓,这也是姓?把这几个姓编到一起凑成一句,真有意思!”父亲又说,这些学校里没有的书,你也要看、要学。还有千字文、三字经、昔时贤文,这都是有用的。”想不到,没有进过孔夫子门的父亲,肚子里也藏着这些东西。原来,父亲不光是要我学会百家姓便于记账,还要我懂得做人的道理,学会立世处事。追悔莫及的是,父亲的话我都当作了耳边风,没能听进去。
还有一天,父亲拿出算盘,要教我打算盘,并一再强调,一定要学会打算盘,懂得算账,以后在社会上就不会吃亏。我在学校里最讨厌的就是珠算课,可是父亲偏偏要我学打算盘,我又不敢说我不学,我很不情愿地跟着他学了几次,勉勉强强知道了怎么打加减法,后来父亲还要教我的九归九除的乘除法,他一边念着口诀,一边拨动着算盘珠,我看着、听着心里直发怵,借口学校上课老师会教而躲过了。学校也确实安排了珠算课,只是我还是没有很好地学会。父亲教我打算盘决不是打得好玩,而是教给我日后生活的本领,可惜我当时没有理解父亲的苦心,后来我在公社里工作时,少不了的统计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那个时期,公社每天要向县里电话汇报当日的生产进度,每天都要做好统计上报,一般的合计还可以用算盘加减法勉强凑合过去,而要计算百分比时我只好求助于人,或是用笔算。如果是一个人在自己本单位统计,没有别人知道也就过去了,倘若是在县里或是区里集中搞统计,就相形见绌丢人了,这就是我没有听父亲教诲的报应!
父亲的算盘是打得很漂亮的,算账的时候,父亲用手把算盘一甩,上下的算盘珠子,上是上,下是下,整整齐齐贴在算盘梁的上下,随后,只听见算盘珠子上下拨动的声音。如果是一个人报数,一个人算,那只要你报得出,你报得多快父亲就算得多快,绝不会让你等着。有时晚上一个人在家算账,他一手拿笔写,一手打算盘,左右开弓,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念着口诀,俨然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老账房先生。父亲的算账、记账的能力和精明,加上他在社交场上的诚信度,不仅是他的同行们佩服,就是古北街上别的行业的老板也都仰慕几分。
二、
严父慈母,严厉、峻酷的父亲,也同样有着母亲的慈祥、温柔。 父亲的严厉,有时电闪雷鸣,近似于残酷,不时地给我们以火辣辣的皮肉之苦。然而,我们又实实在在感受着父亲那座巍峨大山的胸怀里面,蕴藏着的厚重大爱犹如涓涓清流的滋润和和煦阳光的温暖。父亲的严厉中也有柔情似水的另一面,也有着别样的慈祥、温柔!
有一年,大概是我八岁的时候吧,有一天,父亲带我上山砍柴,我们家还是吃农业粮,所以还有分给我们家的柴山。头一天傍晚,父亲就教我磨柴刀、用禾秆打秆扑。第二天一早吃过饭,我扛着勾绳扁担,父亲扛着的是长长的禾杖,我新鲜好奇地跟着父亲,走过牌楼里、周王庙、长山岭。一路上,砍柴的人真不少,也有几个和我一般大小,还有比我还小的。每走到一个地方,父亲就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诸如沙子树下、宝官树下等等,到了自己家的柴山,父亲又带着我在山上转了转,指着周围的山林田地,告诉很多我不知晓的事。然后手把手地教我怎么砍柴,我看了一会父亲砍柴,父亲握着柴刀就像他用卖肉刀一样得心应手,又快又利索,随着右手中的刀一挥一挥,站着的茅柴齐刷刷地在左手中倒下,很自然地一码一码整齐地排在一边。我学着父亲的样子,可是手中的柴刀砍下去却被弹回来了,又砍又弹,再砍再弹,有时碰着了石头子,刀口冒出火花,好不容易被砍倒的几根茅柴也是乱七八糟的。就这样,我砍砍歇歇,父亲一直不停地砍着。约莫过了中午,砍倒的柴已经有一大片,父亲又教我用秆扑捆柴,完了,又教我用勾绳扳担。又另外捆了两个小柴捆让我挑,他自己挑的一担一边有十多捆,比他的个头还高,他用禾杖从柴担子的中间穿过去才挑得起来。我挑着两个小捆柴,这是我第一次挑柴担子,肩膀被压得很不是滋味,一副狼狈样子,父亲笑着说:“呵呵,灯芯换鸡毛喔!”我看着两座小山一样的柴担子压在父亲肩上,随着父亲那有节奏的步履一闪一悠,父亲和我一前一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慢慢跟不上了,与父亲的距离越来越大。大约离家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父亲放下自己的担子,返回来接过我的两捆柴的柴担子,放到了他那小山一样的柴担子上面,我空着两手跟在父亲后面,一路上也有人戏笑我,而父亲却满意得很:“嘿嘿,不错,也试了一下味道,开了一个头!”
父亲也有过给我火辣辣的回忆。我和两哥哥、姐姐小时候都曾经挨过父亲的打,因为父亲心急性躁,一来火就忍不住对我们出手了,可是每次打过后,父亲总掩饰不住内心的懊悔和不安。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情,我挨了父亲唯一的一次打,而且打得真的很痛。那是一次放学回来,只有父亲一人在家,我高高兴兴地一进屋,卖完了猪肉正握着烟筒杆子在抽烟的父亲,突然手中的那支将近两尺长的梨木铜头烟筒杆子向我头上磕来,我躲都来不及躲,被那个铜头子重重地磕了一下,“记得,挨了打,长点记心!”扪着被打得昏痛的头,我想起来了,学校一位老师在父亲这里买了肉,跟父亲说好了让我吃过早饭上学时给那位老师带去,而我急着上学就忘记了。严谨的父亲向来是说一不二,一向把信誉看得很重,当然不允许我犯这样的错误。
父亲就为了这个事打了我一回,而我的二哥就比我挨的打多,他喜欢看书,有的时候因为看书而耽误了父亲的事,也有时是因为他性格活泼,比我顽皮而招致了挨打。
我记得,54年洪水期间,父亲让二哥去上街把合伙轮流使用的船划回来,因为这一天是父亲使用船的时间,父亲把这一天用船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可是一贯喜欢看书的二哥,带了一本书在船上看入了迷,耽搁了父亲的时间,正急着用船的父亲急得非同小可,当二哥划船回来时,还等不到船靠拢,父亲一个箭步跨上船,不由分说,拿起船头上的系船绳子就往二哥身上抽,可怜的二哥原本是很高兴的,却不料被抽得用手捂着腰弯着慢慢的往家里走,父亲见状,三脚两步抢在二哥的前面到了家,跟母亲说:“你快去看看,骗子(二哥小名)被我打了。”母亲颠着小脚跑出来把二哥扶回家,懂事的二哥怕母亲责怪父亲,忙说:“没事没事,就是红了一点皮,就会好的。”经过母亲的处理,二哥已安然无恙。晚上睡觉时,父亲轻轻地掀开被子看了看已经熟睡了的二哥,然后又在二哥身边坐了许久才离开,看得出,父亲满脸的心疼和愧疚之情。
1957年,21岁的大哥被县抽调参加肃反工作,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大哥,一下子就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半年多没有回家,也没有一点消息。都过年了,在外面工作的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家,而大哥仍然没有一点消息。父母亲都急了,父亲几次到区政府打听消息,有的人说他到了四川,又有人说他去了甘肃。刚从县里回家来过年的堂兄永林来看望父亲,父亲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回来了?假仂(大哥的小名)还没有回来呢?”永林哥一听也很惊讶“啊,他还没有回来?我没有看见他呀!”这一下,父亲更像落了魂一样不安神,日里吃饭不下,晚上睡觉不安。大年三十带着我们兄弟到山上点祖坟灯,在我的祖父的坟前,父亲一边点灯,一边哽咽着说“假仂在外面工作,到今天还没有到家,他是你老人家疼爱的,你要保护他在外面平平安安呐。”老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落,洒落在祖父的坟前。
1961年,二哥被录取鄱阳中学高中,那时古县渡到鄱阳只有水路可通,六十里行程需要两个小时,乘坐客班船是七角钱,而且只有下午一班船。开学时为了节省船票钱,二哥跟父母亲说自己步行去饶州府。从岸路走有四十里路程,还有两处扯渡船,一个大人空着手走也要走四、五个多小时,何况一个只有十六岁的孩子,还要担着衣服被子等行李。虽然二哥在家也经常挑担子,如砍柴、挑水,那都是近距离,而这是下鄱阳,有四十多里路,正所谓“长途无轻担”。父亲问二哥:“那么远的路,你挑着担子走得下驾?”二哥回答说:“我早些走,走下歇下,一天的时间还走不到么!”父亲听见二哥坚定的回答,很高兴,想了想,跟母亲商量了几句,“不光是省几个钱,也让他经历经历一下也好”。他决定自己送二哥去鄱阳,二哥更高兴。去学校的那一天,还没有天光,父母亲都早早地起了床,二哥吃过他喜欢吃的腌菜蛋炒饭,稍做休息后,父亲用手掂了掂行李担子的重量,然后轻轻地放到二哥肩膀上,说:“你先担着走起,后面再让我担。”遂接过母亲手中的菜筒,紧跟在担着担子的二哥后面跨出了大门,我也赶紧从竹床上爬起来,跟在母亲身后,站在小院子台阶上,在朦朦胧胧之中目送着二哥和父亲。这时东方刚刚破晓,慢慢地现出一线暗红色,母亲和我望着父亲和二哥的身影,在晨曦中紧紧相贴,一步一步地渐行渐远······
2020年孟秋
2020年孟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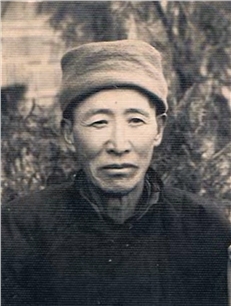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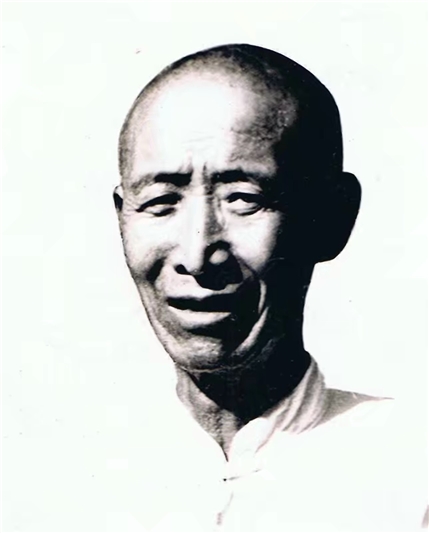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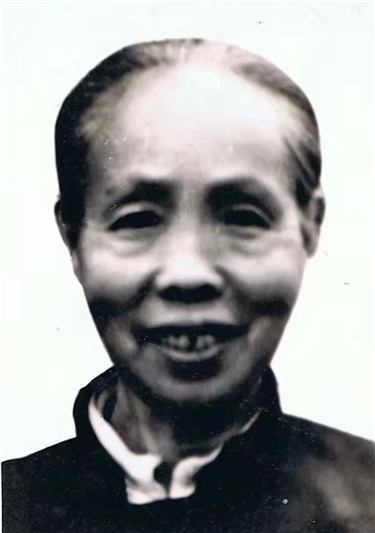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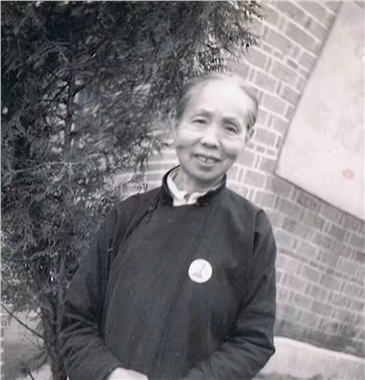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