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巴金与章仲锷的行为写作(上)
我抽出信纸。巴金来信用圆珠笔写在了《收获》杂志的专用信笺上,现照录如下:
心武同志:
谢谢您转来马汉茂文章的剪报。马先生前两天也有信来,我写字吃力,过些天给他写信。我的旧作的德译本已见到。您要是为我找到一两本,我当然高兴,但倘使不方便,就不用麻烦了。
您想必正为作协代表大会忙着。这次会开得很好。我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感到遗憾。
祝好!
巴金
一月三日
说实在的,我已经不记得那是哪年的事了,仔细辨认了信封前后两面的邮戳,确定巴金写信是在1985年的1月3日。
我在“80后”前持信回忆往事,他望着我说:“好啦!你又有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活材料啦!”我听出了他话音里调侃的味道。跟“80后”的后生相处,我不时会跟他们“不严肃”的想法碰撞,比如巴金的《随想录》,他一边帮我往书架上归位,一边哼唱似地说:“这也是文学?”我不得不打破“不跟小孩子一般见识”的自定戒律,跟他讨论:“文学多种多样,这是其中一种啊!”最惹我气的是他那一副“不跟老头子一般见识”的神气,竟欢声笑语地说:“是呀是呀,这是一部大书!好大一部书啊!”巴金的《随想录》,确有论家用“一部大书”之类的话语赞扬,所以他才说这话。
在和“80后”茶话的时候,我跟他坦陈了自己的看法。巴金无疑是写过无可争议是正宗文学大书的,不仅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及其他长篇小说,还有无论从人性探索到文本情调都堪称精品的《寒夜》《憩园》等中篇小说,当然,他后半生几乎不再从事小说创作,他的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李大海》,其中就有《团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那不是一篇杰作,更不能称为他的代表作,但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拍成放映后,影响极大,不过看过电影去找小说看的人,恐怕很少,电影里那首脍炙人口的插曲《英雄战歌》,小说里是没有的,词作者是公木。
巴金后半生没怎么写小说,散文随笔写了一些,我记得少年时代读过巴金写的《别了,法斯特》——法斯特是一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颇活跃的美国左翼作家,写过一些抨击资本主义的小说,但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泄露出来以后,感到幻灭,遂公开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法斯特当然可以评议,但巴金那时写此文是奉命,是一种借助于他名气的“我方”“表态”。这类的“表态”文章他和那个时代的另一些名家写得不少。那当然不能算得文学。可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巴金陆陆续续写下的《随想录》,却和之前的那些“表态”文章性质完全不同,他这时完全是从自我心灵深处,说真话,表达真感情,真切地诉求,真诚地祈盼,这样的文字,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得以激动人心,获得共鸣,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可以为之见证。我眼前的这位“80后”,他也许觉得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那样的著作才算得文学,这思路并没有什么不妥。帕慕克并不是一位“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实际上这位土耳其作家的政治观念是很强的,《我的名字叫红》里面就浸透着鲜明的政治理念。但无论如何帕慕克不能凭借着一些说真话的短文来标志他的文学成就,他总得持续地写出艺术上精到的有分量的小说来,这才能让人服气。
巴金后半生没能写出小说,这不能怪他自己。他实在太难了。“文革”十年他能活过来就不易。粉碎“四人帮”后他公布过自己的工作计划,他还是要写新作品的,包括想把俄罗斯古典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翻译完,但他受过太多的摧残,年事日高,身体日衰,心有余力不足。尽管如此,他仍不懈怠,坚持写下了《随想录》里的那些短文。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写作,我们除了尊敬,别无选择。
“80后”小伙子问我:“巴金给你的信讲的究竟是什么啊?怎么跟密电码似的?”其实也不过二十多年,但拿着那张信纸重读,我自己也恍若隔世。我和巴金只见过一面。从这封信看,我起码给他写去过一封信,这是他给我的回信。“你既然见过巴金,还通过信,前几年他逝世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有文章?”我告诉他,以前的不去算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跟他交往频密的中青年作家很多,通信的大概也不少,算起来我在他的人际交往中是很边缘、很淡薄的,对他我实在没有多少发言权。不过既然发现了这封信,却也勾出了我若干回忆,而与眼前的小青年对话,也激活了我的思路,忽然觉得有话要说。
我跟“80后”小伙子从头道来。而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人——章仲锷。“他是谁?也能跟巴金相提并论?”我说,世法平等,巴金跟章仲锷,人格上应享有同样尊严,他们可以平起平坐。确实,巴金跟章仲锷平起平坐过。那是在1978年。那一年,我和章仲锷都在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当时只有《人民文学》《诗刊》两份全国性的文学刊物,我们北京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同仁以高涨的热情,自发创办向全国发行的大型文学刊物《十月》,一时没有刊号,就“以书代刊”,兴高采烈地组起稿来。章仲锷长我八岁,当编辑的时间也比我长,他带着我去上海组稿。那时候因为我已经于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在文学界和社会上获得一定名声,组织上就把我定为《十月》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章仲锷并不是“领导小组”成员,所以他偶尔会戏称我“领导”。其实出差上海我是心甘情愿接受他领导的,无论是社会生活经验还是对文学界情况的熟悉,他都远胜于我。去巴金府上拜见巴金,我多少有些腼腆,他坐到巴金面前,却神态自若,谈笑风生。巴金祝贺《十月》的创办,答应给《十月》写稿,同时告诉我们,他主编的《上海文学》《收获》也即将复刊,他特别问及我的写作状况,为《上海文学》和《收获》向我约稿。他望着我说,编辑工作虽然繁忙,你还是应该把你的小说写作继续下去。现在回思往事,就体味到他的语重心长。他自己的小说写作怎么会没有继续下去?他希望我这个赶上了好时候的后进者,抓住时代机遇,让自己的小说写作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说一定给《上海文学》写一篇,巴金却说,你也要给《收获》写一篇,两个刊物都要登你的。《收获》也要?那时记忆里的《收获》,基本上只刊登成熟名家的作品,复刊后该有多少复出的名家需要它的篇幅啊,但巴金却明确地跟我说,《上海文学》和《收获》复刊第一期都要我的作品。我回北京以后果然写出了两个短篇小说,寄过去,《找他》刊登在了《上海文学》,《等待决定》刊登在了《收获》。我很惭愧,因为这两个巴金亲自约去的小说,质量都不高。我又感到很幸运,如果不是巴金对我真诚鼓励,使我的小说写作进入持续性的轨道,我又怎么会在摸索中写出质量较高的那些作品呢?回望文坛,有过几多昙花一现的写作者,有的固然是外在因素强行中断了其写作生涯,有的却是自己不能进入持续性的操练,不熟,如何生巧?生活积累和悟性灵感固然重要,而写作尤其是写小说,其实也是一门手艺,有前辈鼓励你不懈地“练手”,并提供高级平台,是极大的福气。
作家写作,一种是地道的文学写作,如帕慕克写《我的名字叫红》;一种则是行为写作,巴金当面鼓励我这样一个当时的新手不要畏惧松懈,把写作坚持到底,并且作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刊物主编,在有特殊意义的复刊号上向我约稿,这就是一种行为写作。巴金的行为写作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十分耀眼,他主编刊物,自办出版机构,推出新人佳作,我生也晚,上世纪前半叶的事迹也只能听老辈“说古”,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和靳以主编的《收获》,我作为文学青年,是几乎每期必读的,留有若干深刻的印象。别人举过的例子,我不重复了。只举两个给我个人影响很深而似乎少有人提及的例子。一个是《收获》曾刊发管桦的中篇小说《辛俊地》,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辛俊地,他和成分不好的女人恋爱,还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地去伏击给鬼子做事的伪军通讯员,将其击毙,没想到那人其实是八路的特工……让我读得目瞪口呆却又回味悠长,原来生活和人性都如此复杂诡谲——《辛俊地》明显受到苏联小说《第四十一》的影响,但管桦也确实把他熟悉的时代、地域和人物融汇在了小说里。这样的作品,在那个不但国内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国际范围的反修正主义也越演越烈的历史时期,竟能刊发在《收获》杂志上,不能不说是巴金作为其主编的一种“泰山石敢当”的行为写作。再一个是《收获》刊发了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的系列短篇小说《童年时代的朋友》,跳出那时期政治挂帅对少年儿童只进行单一的阶级教育、爱国教育、品德教育的窠臼,以人情人性贯穿全篇,使忧郁、惆怅、伤感等情调弥漫到字里行间,文字唯美,格调雅致,令当时的我耳目一新。这当然是巴金对展拓儿童文学写作空间的一种可贵行为。
其实中外古今,文化人除了文字写作,都有行为写作呈现。比如蔡元培,他的文字遗产遗留甚丰,我不敢说其中能有几多现在还令人百读不厌的,但说起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以及跻身学术界后那兼容并包宽容大度的行为遗产,我们至今还是津津乐道、赞佩不已。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固然是他杰出的文学写作,而他一度履行的“文学罢工”,难道不是激动人心的行为写作吗?晚年的冰心写出《我请求》的短文,还有巴金集腋成裘的《随想录》,当然是些文字,但我以为其意义确实更多地,甚至完全体现为了一种超文字的可尊敬和钦佩的文学行为。
“80后”小伙子耐心地听了我的倾诉。他表示“行为写作”这个说法于他而言确实新鲜。他问我:“那位章仲锷,他的行为写作又是什么呢?难道编刊物、编书,都算行为写作?”我说当然不能泛泛而言,作为主编敢于拍板固然是一种好的行为,作为编辑能够识货并说动主编让货出仓,需要勇气也需要技巧。当然前提是编辑与作者首先需要建立一种互信关系。章仲锷已被传媒称为京城几大编之一,从我个人的角度,以为他确实堪列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名编前茅。(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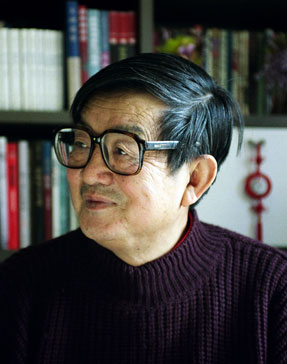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