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夫:深切怀念章仲锷先生
哲夫:深切怀念章仲锷先生
才被动地吃过月饼,不经意间,国庆又不请自来。
推是推不走它了,只好东施效颦。十月一日携伴出游,所到之处悉是煮饺子也似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沉沉浮浮,眉来眼去的,都是红尘的欢喜。人生无非是在浓汤里载沉载浮,不免撩起惘然,节日问候的短信写成一首小诗:淡定、平易、清心、无为,都是有益健康的好辞,非消极,乃自慰尔。想着,放下布袋,就手点起一枝香烟,将许多不如意点燃,丝丝缕缕地吸,再丝丝缕缕地吐,让风儿携走它们,并吹散在远天远地,于是说:阿门!
一个淡定了的自己,一个平易了的生命,一个清心静气的人,便在十月三日起早,写自己的小说。为避免干扰,手机照例是不开的。结束一个工作日已经是晚上,打开手机,却跳出北京女作家熊猫姐姐方敏的短信,上边赫然写道:哲夫,章仲锷今天突然过世,特告知!
心一揪,眼前便出现一个长长大大的身影,在那儿屈体俯身抡臂做跃跃然状,头一回见章仲锷时,是在一个宾馆的活动室,他正和雷达打乒乓球。那时他是《中国作家》主编。帮助和挖掘出许多后来当红的作家。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编之一。以后多次见过,也聊过天。直到他离退回家还保持联系。这一切,其实是得益于他的夫人高桦,我们都叫她老太太。可以毫不夸张的这么说,高桦年轻时是个阳光灿烂的女人,老来时也是个灿烂阳光的老太太。
高桦是《绿叶》杂志创始人,也就是说,她是中国最早启蒙和倡导环境文学的一个了不起的老太太。从那时候起,她剩余的生命几乎全部耗费在扶持环保文学事业上。我和老太太的相识,便缘之于此。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哲夫文集》十卷本,在中国作协举办的讨论会就是由老太太一手操持的。那是一次开得很成功的讨论会,会后我便弃小说而写环保纪实文学至今。类似这样的环保文学会议高桦主持过的何止一次两次。只要是中国有点名气的环境文学作家,几乎都认识她,都得到过她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帮助。
最后一次见面在山西,章仲锷做心脏手术后恢复的很好,人比过去有些胖。高桦还是那么健谈,章仲锷还是话不多,偶尔蹦豆似地来一句,也就几个字。之后有段时间没有多联系,大约一个月前,高桦突然打来电话,要我参加国家林业局野保办的活动去江西写梅花鹿的报告文学,奥运在即,我不想错过精彩,就说要去就往后推,一推到了现在。老太太还健在,而相濡以沫的老伴却已经不在。我在悲痛章老逝去之余,浮上我心头的是一种担心和疼痛:苍天不公,这对伉俪情深一辈子的老太太打击实在太大了,这痛苦她承受得了吗?
这个它,如同挡不住的访客,遑论你接受不接受、欢迎不欢迎、邀请没邀请,它总是近乎厚颜无耻地不请自来登堂入室又居心叵测刻不容缓地不告而辞。罔顾你是哭是笑、是悲是喜,是贵贱尊卑、是美丑善恶,是路无拾遗还是饿殍遍野,是金戈铁马还是风花雪月,它来时无遗巨细绝不肯把你放过,去时也不遑亲疏绝不肯把你眷恋。它目空一切,视天地为无物,创造也罢,自毁也好,植玫瑰是你闻香,种恶果是你自食,任凭洪水猛兽天崩地裂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南极冰雪融化,悉数儿,它照单全收,我行我素,全无一丝一毫的怜悯。
方敏在给我的短信中说:我给老太太去电话,她女儿接的,老太太手机不开,现在也接不了电话,一接就大哭,说不成话,你可过几天再打。九号去八宝山……
这个它,无始无终,无形无质,如影随形,日每逼近你没商量。这个它,不离不弃,变幻莫测,有形有色,分秒算计你不含糊。光怪陆离地堆砌文化、积淀历史、造化人类社会,不眠不休,神工鬼斧地塑造抽象、雕刻具体、伴随自然生态,不离不弃。这个它,只有我写给自己这首小诗还可以勉强应对,不妨谨记:淡定争上游,平易人长久。清心真美酒,无为足风流。
章仲锷
《忧天·佑地·幽思》(重庆出版社,1992年)。短篇小说《浸血的白花》,1979年《上海文学》;评论《评〈严峻的日子〉》1978年《人民文学》,《馆蘸生命谱战歌》(1978年《解放军报》)《泥香扑鼻报春来》(1979年《工人日报》)等作品。以大量的杂文、随笔,出有杂文集《忧天·佑地·幽思》(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编发过获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第二个太阳》,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有《蒲柳人家》、《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沙海绿荫》、《太子村的秘密》、《远村》以及长篇小说《新星》、《玫瑰门》、《玩的就是心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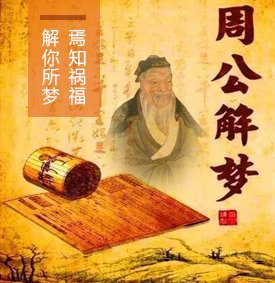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