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卡赞的情欲地貌
周日,卡赞先生离世。而紧随他的新闻讣告罗列了他生平的经典影片,那简直就是方法派的大事件集。参与他执导的影片的演员,有马龙·白兰度,曾在《欲望号街车》中大喊过“斯特拉!”,在《码头风云》对着罗德·斯泰格尔低语过,他本来会是一个竞争者;有詹姆斯·迪恩,《天伦梦境》的男主角;有沃伦·比蒂,他出演过《天涯何处无芳草》,一部青春期的爱情剧;有出演《娃娃新娘》的艾利·瓦拉赫与卡尔·莫尔登,两人在剧中被性感的密西西比蛇舞和经济对抗搞的精疲力尽。
卡赞曾与人创办了“演员工作室”,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在百老汇的舞台剧与好莱坞的电影事业都如日中天。是他,使美国人对戏剧性的写实主义影片有了鉴赏力,他的方法派表演风格也在日后的美国电影中大量涌现。那种欲言又止,含蓄内敛的情绪展现方式取代了早期那种程式化的说辞与古板正规的动作。社会问题,潜伏的情欲和内心的真相成为舞台与荧屏上严肃的化身。
在任何艺术形式中,或许特别是在给人以透明感的错觉最强的电影中,现实主义,是
一个以狡猾而闻名的词汇。在今天看来,卡赞的电影可能比那些社会及心理寓言少了些生活的片段;他的电影里有更多华丽的辞藻,人物的思想境界也更加崇高。这是他影片中一贯保留的,也因此使他们流传至今。他的影片是道德冲突与多变的欲望的喻本,是那些被愤怒驱使、反叛却偶尔会做些正确的事的男人的个性研究的典范。没人会真正喜欢斯坦利·考瓦斯基,或者喜欢《登龙一梦》中安迪·格里菲斯饰演的那个野心勃勃要当政客的乡下小子。即使现实中的艾米丽艾诺·萨帕特并不像白兰度在影片《萨帕特万岁》中演绎的那样,人们有时还是更喜欢现实主义而不是真实的生活。
卡赞生前所受的批判性评价似乎有些勉强:他是导演主创学派的一个名导演,但最多只算是二等人物;他的影片及御用演员们都受到欢迎与肯定,但与他的朋友及同行们比如尼古拉斯·雷一样得到的桂冠却遭到了否定。 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卡赞的电影跟尼古拉斯·雷的不同,他的电影很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对大众和奥斯卡评委来讲,他的电影通俗性强,对严肃的同时代话题做了真心的承诺,有时体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崇拜,就像影片《君子协定》、《荡姬血泪》和《码头风云》中所表现的那样,而这些却被一些人认为是缺乏艺术性,透着令人失望的平庸。
玛丽·麦卡锡,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间,《党员评论》杂志社里的一位重要人物,她以对美国戏剧现实主义持强硬批判态度而著称。她的异议总结如下:当今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看过至少一部田纳西·威廉姆、威廉姆·英奇或者阿瑟·米勒的戏剧作品,至少一部卡赞导演的电影。据我所知,他们的观点,仍旧停留在剧院出现以前,他们认为剧院是个老古董。当然,她的总结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卡赞的现实主义,就像阿瑟·米勒(卡赞曾在百老汇导演过他的戏剧)和约翰·斯坦贝克(与卡赞合作过“帕萨特万岁”和“天伦梦觉”的导演)一样,确实有些陈腐的样子。但是这些精神食粮虽然冒犯了一些鉴赏家的精细品味,却也提供了许多诚实的养分。
今天,我们要奉承《君子协定》中的教训主义是件很容易的事,在该剧中格雷戈里·派克假扮成一个犹太人(事实上他也被认为是犹太人),揭露并斥责反犹太主义。但在1947年,话题需要制造,并且还得悄悄准备好听众。《荡姬血泪》,讲述一位白皮肤的黑人妇女被当成白人,这样的情节在今天看来呆板做作,像俗气的闹剧;但在1949年它主要是直白地反映出令人痛苦不堪的人道主义。二战之后,这类电影在美国人对种族划分的态度上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胶片会在时光流逝中褪色,但是卡赞自50年代以来的作品依然富于生命力,这不仅是因为白兰度和迪恩这两位名演员。伴随着他的电影,或者说他在电影上的代价,在麦肯锡时代他意识形态上的传奇般的角色被众人所牢记。他即作为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自由领袖被人们念念不忘,也带着背信弃义的恶名遭人唾骂。
到底,他是像诋毁他的人声称的一样,背叛他自己的原则,把名单给了反共调查委员会,还是像他自己坚持的那样,他是在试图无愧于他们?现在平复争论或者解决他生涯上的矛盾已经不重要,他的电影就能说明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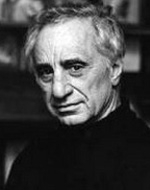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