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光琰像当时中国无数的臭老九一样,成了被打倒的对象
最近几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剂--各种酶--不断被发现,成为现代生物化学的重要领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业污水处理,等等。这证明萧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对未来的学科方向看得非常准,相当有预见性。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萧光琰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和聪明才智,他努力工作,这期间完成了很多论文。1964年大化所承担国家急需的“大庆中油加氢裂化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课题攻关任务,萧光琰为催化剂最后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工作成绩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当了侨联的副主席。1964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当了室主任。
那时他曾经找到我,说他想见一见已经十年没见面的哥哥,如果他哥哥不能来中国见面,是否可以到香港见面?他希望他的哥哥也能来中国工作(他哥哥当时在美国的保密单位任职)。我当时听了,很感动。在历尽人世沧桑的今天,我觉得他在多次挨整之后,还想让他的哥哥也来中国工作,太天真了。
1964年末,我离开大化所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和现在没法比,此后,和萧光琰的直接来往就很少了,只是从到北京开会、办事的人那里听到些零星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走向极点。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每天挨斗。
我经常被拉出去游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时,给我挂个大牌子,我们手里还拿着盆,拿着棍,一边敲一边跟着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儿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着回家怎么向他们解释。回家后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准备了好饭好菜,想用这种办法安慰我,我知道瞒也瞒不住干脆直话直说,“今天我被游街了,给我挂个大牌子,写着‘打倒铁杆保皇派白介夫’,不过我一看,旁边那人挂的牌子上写的是‘打倒钢杆保皇派×××’,心里想,还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来。
另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给我带了顶常见的很高很尖的纸帽子。不知谁想出来新花样,给我旁边那个挨斗的人戴了顶老戏里县官戴的帽子。两边有两个大耳朵,斗他时一按他的头,两个大耳朵就跟着一煽一煽的,我看着觉得很可笑,虽然在挨斗,心情并不坏。这时候,突然有个造反派党委副书记,年纪比我还大,上台狠狠煽了我两巴掌,以表现他的革命精神。那时有很多这样的人。
人有群胆没有孤胆。那时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里不太紧张。在挨斗时,周围很多人,特别是所里的工人对我仍然特别好。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这时一个外号叫唐二愣的工人,对着造反派大叫了一声:“别让他跪着,他跪着也比你们站着高。”我当时心里真是感动。唐二愣马上也进了专政队,他出身好,什么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久,造反派让我收拾东西,我知道以后就不许我回家了。那时候周围已经有不少人自杀,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华(科学院的副秘书长)。我曾参加抗日,有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历史背景,记得当群众敲锣打鼓开除我党籍的时候,我很自信地对家人说,如果我被开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开除。我长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样在尽量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保护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较平和,不很激烈,总是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这些因素都使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有较强的耐受力,即使这样,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难熬,很理解人为什么会想到自杀。
我被关在专政队时,常常会想到过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么样了?我常常想到萧光琰,很为他担心。萧光琰的历史背景不能给他任何保护,他的思想行为和当时的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说他像个玻璃制品,透明,坚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国话都讲不流利,他们一家怎么度过这场灾难?他们挺得住吗?
我被放出来不久,就听说了萧光琰的遭遇。我这么不爱激动的人,却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
走向深渊
根据我对萧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围人陆陆续续的述说,他生活的最后片断,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闪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萧光琰像当时中国无数的臭老九一样,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样,挤进其他几家人。住进来的人要共用厨房、厕所。这对很习惯保护隐私的萧光琰来讲,是太不习惯了,突然,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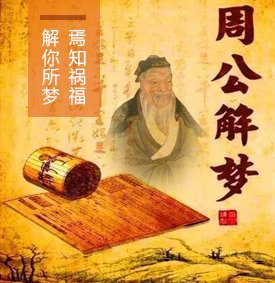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