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光琰是个不掩饰自己情绪的人
综观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不力,妥协退让,加上“六无六净”的“右倾言论”,市委领导就把我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连市委让我停职反省,每天在家写检查。当时整我的势头很大,我心里清楚这里的内在起因:得罪了市委书记夫人。虽然心中无愧,失去工作,停职在家写检查,也还是有很大精神压力。
在自己对党的事业充满热情的不惑之年,无端挨整,使我对于“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态滋味,对萧光琰和其他在运动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涡里,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是何等地无能为力!表面上每个人的批判都是从革命事业,党的利益出发,其实政治清算背后,掺杂了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装扮得大公无私来悄悄地获得私利。
我被停职这段时间里,没再去打网球,和萧光琰在一段时间里就没有了多少联系。
又见光明
当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报到省委以后,省里派人下来调查,发现实在是没有什么事实,下面的人都替我说话,所以就决定不给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约在家里呆了半年以后,恢复了我的职务。这次停职反省,使本来个性不强的我变得更加谨慎。
我恢复工作以后,很珍惜工作机会,和张大煜所长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张大煜长在中国,到德国留学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国文化。他工资很高,可十分节约。工作中他个性随和,能变通顺应,迂回解决问题,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记,却不会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张大煜勤奋刻苦,对化学领域里的科学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选题上很有前瞻性,广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学问以外,他没有很多其它的个人爱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优秀知识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领域里保持领先的学术地位,张大煜功不可没,是一个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科学奠基人。
当时张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实用科学,科学家们可以更放心大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我给与全力支持。这在当时对科学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时我受科学家们的熏陶,产生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学科方向,这样在基础理论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动科学事业;另一方面,必须有结合实际的题目和项目,这样科技人员才会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会价值,产生更大的科研热情。
我和张大煜交流了这些想法,决定和一些技术骨干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于是1962年大连化物所在青岛开了一次会议,解决大化所科学研究的大方向问题。这就是对大化所的未来有重大影响的“青岛会议”。这次会上,我们还明确提出要培养年轻人。在科学领域里,很多重大发现都出自年轻人。当时选了10个年轻科学家作为技术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他们中有六个后来当了科学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员和设备,让青年科学家放手干。同时确定了党政工作人员要为科研人员服务的指导思想。
那时从上到下还是提倡自我批评。所里进行了“解疙瘩”等拨乱反正的活动,对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中的一些过火做法进行纠偏,运动中有些有过激言行的人还诚心诚意地向萧光琰赔礼道歉。我也很真诚地向在过去的运动中挨整的人道歉,当然包括萧光琰,希望他们不计较运动中的过火行动。萧光琰很兴奋。
萧光琰是个不掩饰自己情绪的人。当他感到作为一个人受到应有的尊重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又开始常常邀请一些年轻人到他的家里,用水果、点心和糖款待他们,和他们谈工作,谈学习。
他请年轻人教他夫人学中文,让他夫人教年轻人学英文。看到有的年轻人的英文不好,买来英文小字典送给他们,让他们多背多记一些单词。他认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须学好英文。他努力用实际行动改变和周围的关系,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是无意识的。人总是会被潮流裹挟的,萧光琰在慢慢地改变自己,试着融入这个社会。
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运动,萧光琰的失眠也奇迹般地好了。心情的舒畅使他恢复了科研热情,产生了很多创造性的思维,又开始专注地搞他的催化剂。当他读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时,立即联想到化学催化剂,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于体外的生物或化学反应。这个想法,使他很激动。当时在大化所没有搞生物催化剂的条件,当他知道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就要求兼任那里的研究员,以满足他对催化剂事业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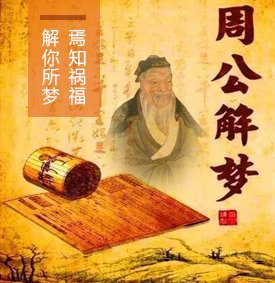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