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与张有天相处的岁月----鲁永恒
回眸与张有天相处的岁月
-------纪念张有天逝世四周年
鲁永恒
张有天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挚友和师长。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应该是忘年交了。他先后在吉林省石头口门、亮甲山、星星哨、庙岭、新安、黄河、察尔森水利工地工作,十几年来,水利工地留下了他辛劳的足迹,也留下了他的青春和理想。虽然他离开我们4年了,可我们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的情景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初识有天是1968年的事。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我和同班的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同被分配到了省水利工程公司四处吉林市舒兰县亮甲山水库工地。一切都很新鲜,到了亮甲山没几天,上边就宣布工地实行军管,说为了搞好工程建设,在工地不搞文化大革命,所以那里基本上没有发生武斗等事件。亮甲山工地聚集了省内知名的水利专家、能工巧将,其中就有有天。与别的技术人员很不一样,他一米八十多,高挑的个儿,平头,看起来很文静,皮肤白皙,书生气十足。他住在工程科那边,离工地很近,也时常在工地绑钢筋。那时我们接触并不不多。
那是个深秋,亮甲山工程基本结束,工地只留少数人扫尾,其余人员统统去了永吉县的庙岭水库。离开了亮甲山,军管也随之结束了。那时候正值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清理阶级队伍的标准基本上是一看历史,二查现行,只要有人提名,可能就要整一顿,开会批斗。文斗算是文明的,不合作的也少不了挨上三拳两脚。有天对人和气,工作认真踏实,又没架子,加上平日和别人没什么过节,工地的造反派也就没有找什么麻烦,在庙岭算是躲过了一劫。有天个子高,工地上没有不认识他的,平日里他穿着极其平常,除了工地发的工作服,就是那个时代的蓝色制服了。一次,他从家里出来,一件放在兜里的重要东西丢了,后来发现新衣服的上衣兜是漏的,兜底压根儿没有缝!他的心思几乎全在工作上,从不顾及衣着打扮,他的头型从我认识他就没变过。有个工程师冯允伦(50年清华大学毕业)没那么走运,被揪出来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大会、小会批斗,每天有固定的程序,后来发展到了挂板牙(挖掘机的斗齿)批斗。拨乱反正后,冯允伦担任了吉林省水利厅总工。
记不清确切的年份了,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了有天家。因为我家也在长春,过年总要回家的,我们有时同行。他家离我家不远,那是个筒子楼,他家住一层,屋子还不足10平米,我感叹太小了,他们告诉我这已是改善后的住房了,先前的房子只有6平米,看得出来,那时他们还是相当满足的。有天186米的个头儿,他的夫人也是一个大个儿,女儿也上小学了,他们一家3口就住在那狭小的房间里。房间极其简陋,靠窗户放了一张旧两屉桌,房间右侧放了上下两张单人床,下面的床还加了一条可以折叠的木板,平时木板放下来,过道会宽敞些,有天在家时,木板支起来就成了双人床,女儿睡在上床。房间左侧靠墙放了家里最贵重的家具---缝纫机,一进门的右墙角还有洗脸盆架,再就是一把椅子和小板凳了,屋子里满满当当的。有天是很感激他夫人的,因为他常年在水利工地忙碌,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回家团聚。几乎是她一个人承担了家中的一切,把女儿养大。
勾起我最多回忆的是我们在磐石县黄河水库工地施工的日子了。大约是在1970年秋,刚到工地时我们住在一个土房里,工地没几个人。晚上老鼠经常光顾,有时会碰到你的手脚。后来工地逐渐人多了,我们架起了棉帐篷,一个帐篷约有十几米长,里面靠一侧搭起通长的板铺,这就是有天和我们十几个人的大通铺。东北的冬季极其严寒,地中间支了一个烧煤的炉子取暖。我们大约住了两年帐篷,指挥部给我们雇了个当地的朝鲜族老头看帐篷带烧炉子。帐篷里不像土房里那么潮湿,但是老鼠多的出奇,一旦熄灯,老鼠立刻从四处窜出来,似乎屋里压根儿没人。我们决心与老鼠战斗一番,我们设计了战斗方案,既简单又好用,大家每人手里拿块砖,对准老鼠常走的地方,然后熄灯,等一小会儿再开灯,十几块砖头飞向老鼠,每次都能消灭几只。当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充满了欢乐。帐篷是我们的家,家里有工人,有技术人员,还有队里的领导。
黄河水库位于磐石县明城和烟筒山之间。是一座失修的中型水库,我们的任务是给水库配套溢洪道和闸门。那时候,修建水利工程项目很不容易,工程必须的钢材、水泥、木材都十分紧缺。在黄河水库,有天是工程项目的总技术负责人。为了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任务,他提出设计钢丝网双曲扁壳钢筋混凝土闸门的方案,这个方案可以解决因工程急缺钢材而上不了马的问题。他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支持。自此,他投入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从设计、计算到实验、施工,无一不亲历亲为。为了取得玻璃纤维的材料物理指标,他跑图书馆、省石油设计院查资料;为了得到理想的混凝土配比,他亲自制定实验方案,跑铁路工程材料实验室;为了闸门的保护涂层方案,他跑九台化工厂,请能人;为了加工闸门支铰,他跑吉林水工机械厂、永吉县农机厂;为了保证闸门钢丝网双曲扁壳的质量,他和高振阳等技术人员、工人师傅共同反复研究施工方法,直到质量满意为止;为了取得闸门工作荷载下的实验数据,他亲自设计原型实验方案,跑东北勘测设计院,请东北院水科所的同志到工地进行原型实验研究,他自始至终亲身参加实验。因工作需要,他经常要出差。从水库工地出去要翻过一座山梁,再走四五十分钟的路才能到烟筒山火车站。不翻山就得绕路走,需要更长的时间,偶尔才能搭上方便车。从工地到烟筒山这段路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足迹!一次,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里,他出差未归。有人认为风雪太大,估计大张(由于他个子大,人人都喊他大张)回不来了,但却也有人认为,他一定会赶回来的!果然,在深夜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身上飘满了雪花,深夜赶回了工地。有天平时还要审查其他相关的工程设计图纸、甚至是算稿。在工程设计中,他尽力采用先进技术。在闸门设计上,主要受力构件采用了预应力芯棒技术,这在当时水利工程中绝对是一项创新;在梁柱框架结构上镶嵌钢丝网水泥双曲扁壳面板,闸门整体结构受力合理;闸门正面采用玻璃布加改性环氧树脂涂层的保护措施,闸门呈银灰色,外形美观。张有天还和施工组织负责人冯文奎及工人师傅等共同研究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组织设计,实用而新颖的施工方法应运而生。钢丝网双曲扁壳、钢筋混凝土预应力芯棒及闸门铰座钢结构先行加工预制;闸门整体采用立体交叉一次成型的施工方案,木模工、钢筋工、混凝土工、架子工交叉连续作业。如此复杂的施工方法在他和他周围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师傅手中成功的实现了。那时候,黄河水库溢洪道工程成了当地的一道美丽风景,一时参观者络绎不绝。至今我还保存着有天拍摄的我们在工地合影的照片。黄河水库钢筋混凝土闸门还被收入水电部技术革新选编和华东水利学院、大连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合编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一书中。它是吉林水利工程队的作品,首先是有天的作品,它凝聚了他的心血。
有天的科学工作态度、勤奋拼搏的工作作风和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在他的工作中无处不在。黄河水库工程方案论证初期,他曾和我谈起过他的设想,能否在那里搞个虹吸式自动排洪工程,因为水库上游有明城镇和沈吉铁路线,下游有烟筒山镇和沈吉铁路线,水库的调节能力较差,如果能够搞个能自动排洪的工程是否可行呢;他通过各种方式收集资料,了解国内尽可能多的工程实例,学习有关工程的设计、施工、及运行经验,对工程方案进行调查论证。记得他曾和北京火车站工程设计者进行书信交流,探讨双曲扁壳在水利工程应用的可行性,还写信向有关专家请教,探讨有关的工程技术及计算方法。他在70代初就尝试使用计算机进行工程计算了,不过那时候用的电子管计算机,很不稳定。吉林市水利勘测设计室的同行经常称他张老师。张文锦称赞有天,说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工作中对我们有很多帮助”。这应该是对有天的中肯评价。有一次,工程队的一位技术员找有天,请他帮助校核厂房桁架的承载力。他除了认真检查算稿外,还帮助设计了原型承载力实验,并亲自动手帮助做实验,取得了理想的结果,让那位技术员非常感动。有空的时候他经常阅读英文书籍,他说,有一天我走不动了,我就作文字翻译。在黄河水库施工时,曾有一名下放附近农村的女医生慕名来找有天,提出要向他学习英语。我们分开后,他去了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继续他为之奋斗的水利事业。我听说他正在察尔森工地搞岩洞的喷锚支护---那也是一项首次在水利工程应用的新技术。过了两年,我离开水利工程队来到长春水电学校工作。一次去镇赉开会,和水利厅的车轩处长在一块儿聊起有天,车局长有些兴奋,他讲起了尘封的往事。他说那时候他是石头口门水库工程局的一把手,是张的领导。他感叹说:“张有天真是一个人才啊。那是在石头口门水库施工建设的日子里,入冬了,工程基本停工,但工程进度吃紧,领导压力很大。有天提出了一个利用冬季冰冻湖面承载力备料,做施工前期准备的方案,他对冰面承载能力进行了精确的计算,如果成功,施工期将大大缩短。考虑到冰上运输风险太大,开始我没有同意,但他竭力说服我。为一项合理的建议,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厌其烦地找我。当他最后那次找我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张有天真的没有私心,他的精神和态度真是值得称颂的。为此,我召开大会,表扬了他,也采纳了他的建议,工程进度因此大大加快了。工地技术人员的思想也得到了很大的解放”。要知道,那时候有天还是个刚刚摘帽不久的右派,车轩是石头口门工程的一把手,如果没有有天给他的感动,没有那充满了科学精神和智慧的建议,试想,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谁会去拨动那根敏感的阶级斗争的神经呢。80年代后有天到水科院工作,又去西德亚琛作访问学者。他十分珍惜回到水科院的时光,不愿浪费每一分钟。我到北京出差时总要去看他,每次到他家,看到的都是满桌的资料和书稿,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
和有天在一起的日子里,大家相处的非常融洽,他为人宽容,心胸开阔,与人为善。在同事、朋友面前他从不摆架子。在那个年代,他除了要承受工作的压力,经常还要承担精神上的压抑。记得,那时工程队领导在作工作总结时,有一条也是必备的,那就是在总结了工作成绩之后,总要提到自己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只抓业务,忘了政治,重用了坏人,例如冯允伦、张有天。但有天从不往心里去,从不与领导争辩,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比起前些年不能搞技术工作劳动改造的时候,他已经感到很满足了,他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闲暇之余,他还喜欢和年轻人一起玩,如打牌、下棋都是他的强项。在新安水库工地施工时,晚上的灯光时常是昏暗的,不能看书。为了锻炼自己的记忆和专注力,他就尝试和别人下盲棋(不看棋盘),他躺在火炕(东北农村的土炕)上,其他人围着桌子上的棋盘看热闹。他也常和年轻人开玩笑,但从没红过脸,也从不在意自己的什么学历、身份等等,和大家很随和,即便是大字不识的工人,也能和他搭上腔。
同事们在谈起与有天一起工作、生活的的往事时,无一不称赞他的人品和才华。在吉林省工作的十几年,他始终奔波在水利工地的第一线,在吉林省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为人热忱,工作孜孜不倦、充满了科学创新精神,在那社会丧失公平公正,人性泯灭、知识分子饱受欺凌的年代,他曾经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磨难、肉体摧残。但他没有倒下,他是我认识的受过冤屈而毫不沉沦,笑对人生,乐观向上的寥寥少数人。他是一名人格高尚、才华横溢、充满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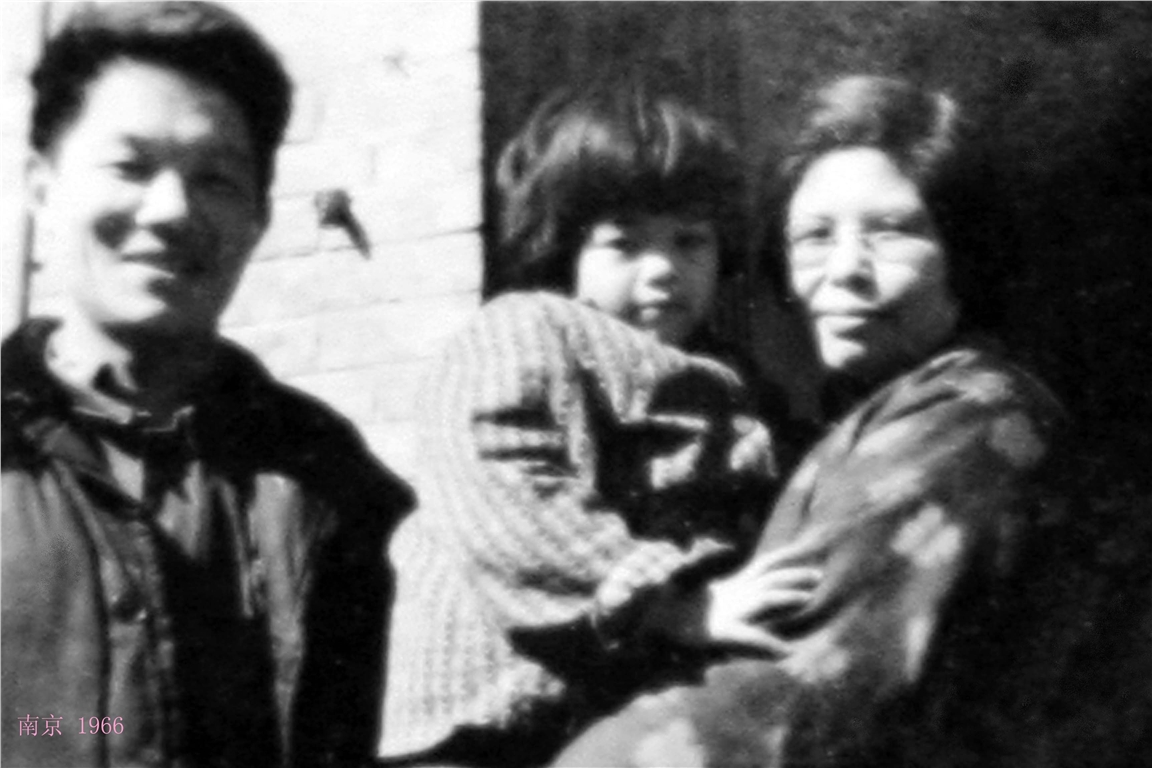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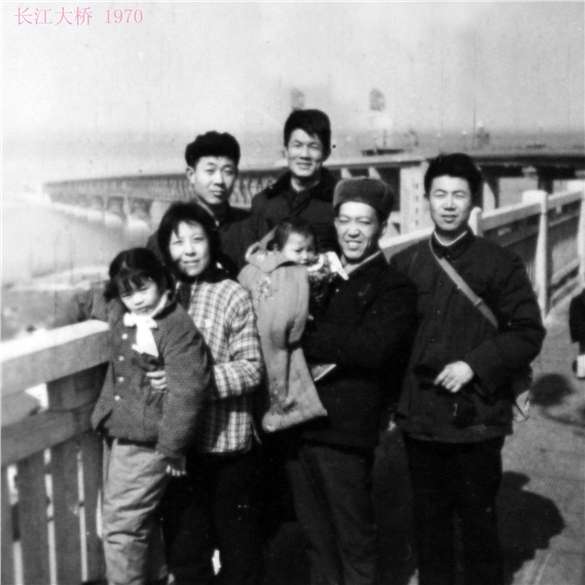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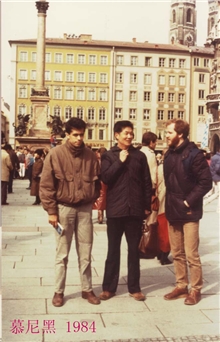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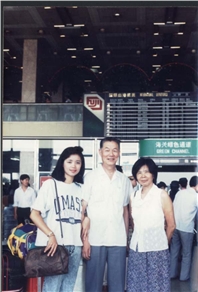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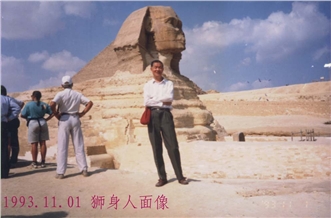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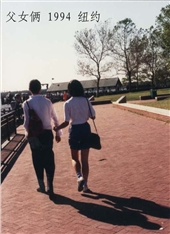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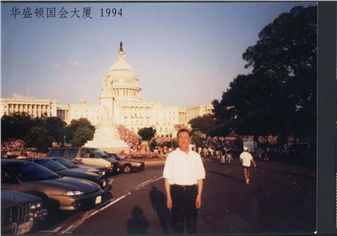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