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民间去,我从民间来。——悼著名民间诗人邵春光(邵揶)
你从民间去,我从民间来。——悼著名民间诗人邵春光(邵揶) 文/廖蕙琳
今天我有些失落
放弃所有的时间
沉迷于Michael Jackson的【Billie Jean】
就让时间停止吧 让我对着我的思维发呆一会
这些粗心的家伙们
总习惯将民间的卜告封锁些日子
从民间传来的消息是否慢了些?
民间的速度到底是慢了些时日
你是沾了月亮的光了
还是有人会忆起你
你的郁郁兄弟足以打动你诗歌里所有汉字
我寄居且奔波于南京的大街小巷
连走路都不忘给你写几句放在手机里
我只作为房价的见证人
看它涨就涨——这脱缰的野马、欲望
是无法让一诗人驾驭的
就 让裹尸布收尾吧
2010-3-10 写于南京
中国著名民间诗人邵揶(邵春光)不幸于2月27日12时39分在长春人民医院病逝,享年55岁。
邵春光,笔名邵揶,1955年1月5日生,山东青岛人,早年随父母迁居长春。一生爱好文学创作,曾著有《阿图瓦的冬夜》、《加农炮》、《水手情潮》、《民族唱法》等十六部诗集及同名CD专集。1985年至2005年间创办民间刊物《太阳》,其作品在中国诗歌圈内有较大的影响力,部分经典作品至今仍在网络中流传,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专题记录片《黑土地的春光》向世人展现了他不平凡的一生。2005年邵春光先生因病中止了创作,长期在家中静养。
邵揶曾做如下的自我介绍——
老少这人走路时很随便
老少活得很随便
老少随随便便地结了婚
老少当腻了儿子想当当老子
就让老婆产下了一个
披着人皮的虎羔
老少牵着儿子到处游荡
去动物园欣赏狐狸
去百货商场诽谤玩具
老少教儿子吃猪狗食……
——(《老少这人》)
后现代主义文学对神圣和崇高的消解,在中国是从邵揶开始的(邵揶是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在此以前,中国当代的文学一直戴着神圣和崇高的面具,这副面具掩护了多少荒谬和虚伪!消解神圣和崇高,并不是反对真正的神圣和崇高,而是要剥去戴在荒谬和虚伪身上的面具,让生活的和事物的本来面目裸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在上面这首诗中,老少痛快地剥去了关于人生和时代的所有冠冕堂皇的语言伪饰,让一个城市贫民(虽然他同时是一个诗人)的寒伧、卑微和穷困活生生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而构成对披在时代身上的那层纸糊七彩外套的一个揶揄,一次嘲弄。
在另外一些诗中,邵揶的这种揶揄和嘲弄更有一种入木三分的力量,比如他写于1993年的《当尸布盖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当尸布盖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我们会想起他的生动
……
是的,就算尸布托起的灵魂
曾有罪过
谁还愿意再记起
死亡的苍凉
最能让丑恶变得美丽
冬天的树梢被落日映照时
乌鸦也是金色的
读这首诗时,我想起鲁迅的散文诗《立论》: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我无意于拿邵揶和鲁迅作比,但邵揶这首《当尸布盖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在揭露人类的虚伪这一点上,确实和鲁迅的《立论》有同等的穿透力和震撼力。
在人类生存的旷野上,邵揶只是一头羸弱的羔羊,但在人类精神的荒原上,邵揶却要做一头有着百分之百野性的狼。他写于1987年的一首《狼子之心》,其实是他的夫子自道:
父亲说狼比狗好
不用靠人养活也不用
不停地摇尾巴
外婆说狼好是好只是
狼不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不像 、狮子和豹……
在我的感觉中,邵揶就是北方荒原上独自嗥叫和奔走的一头狼。他绝不是被喂养的家禽,也不是被驯服的鹿和马,更不是被保护的珍稀动物。他以自己的粗鲁、野蛮和绝望嗥叫着,他以嘶哑的喉咙在阴郁的天空下嗥叫着。这嗥叫带着对既定秩序的挑衅和蔑视,对所有奴性人格的嘲弄和厌恶。
邵揶的诗不仅仅是冷嘲热讽,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他有着一副不易为外人发现的悲天悯人的心肠,但他从来不会摆出那种愤世嫉俗、替天行道的架势,也从不装出楚楚可怜、长 吁短叹的模样,而是冷静、克制,间或带点苦笑,如《没有月饼的中秋》:
所有的节日
永远只属于有钱的人
流浪在月光下的眼睛
只能对着天上的月饼发呆
这样也好
一个人在月光里徜徉
什么也用不着有,没有月饼
就用不着去咬破中秋
用不着去咀嚼月下的往事……
写人间的贫困和不幸,臧克家有他的《老马》,艾青有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和艾青的诗通过对苦难的描述,唤起读者对苦难者的同情,诗人多多少少表现出一种救世主的姿态,但在邵揶的诗中,救世主的姿态被彻底颠覆了。苦难者拒绝同情,甚至拒绝承认自己的苦难,这并不是阿Q式的精神安慰,而是立足于人的尊严。另有一首《月光奏鸣曲》也写苦难和贫穷,它甚至是邵揶真实人生的记录,但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邵揶在发泄个人的哀怨,那就失之无聊和浅薄了,因为邵揶从来不是一个顾影自怜的人,更不是一个试图通过展示自己的不幸来企求同情和怜悯的人。这首诗,是邵揶通过记录个体人类的生活境遇(哪怕确实是邵揶自己的境遇),来描述人类普遍的生存窘境和永恒的孤独:
月光罩着辘轳
罩着打结的井绳
月光罩着敞口的麻袋
罩着泛着酒香的酒糟
月光罩着横七竖八的玉米秸
罩着铡刀……
月光罩着反刍的牛
罩着八头反刍的牛……
月光罩着我
罩着我身下
越来越凉的坑……
月光不罩
我散落在阴影里的诗稿……
邵揶反对浪漫主义的泛滥的激情,反对现代主义的膨胀的想象,他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的目光省略了尘世表面上的繁华和喧嚣,而把他的笔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那样对准了人类的伤口乃至隐藏在暗处的疾患。
邵揶的某些诗作有很强烈的哲学意味,几乎像闪电一样擦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昏昏欲睡的灵魂为之一震:
幸福/不过是牙疼和牙疼之间/那一小会儿/不疼(《幸福》)
光有情人还不够/还要有仇人/这样才能像个英雄/不使冬天的麻雀啄开薄薄的雪/
寻你草籽一样的生命(《阿伦兄弟》)
似乎是随意说出,其实是作者对生命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感悟,一种对人类生存奥秘的独特发现。有些诗人用深奥繁复的诗句来说出肤浅的道理,邵揶却用最通俗的口语说出了人类生存的秘密和世界的。
邵揶的诗歌尽管在淋漓尽致地消解着神圣和崇高——但那能被消解的神圣和崇高,恰恰是虚伪的神圣和崇高,面对真正的神圣和崇高,邵揶便情不自禁地严肃起来,比如他写《文森特·凡·高》:
你本能地闭上眼睛,因为
你把脸仰向了太阳
左轮 的枪管,抵着你的右肋
枪柄在你手里
接下去的事你料到了
会有一小片麦子
在你身下倒伏
接着是一种暖烘烘的颜色
顺着折断的麦茎
渗进泥土……
语气是如此庄重,我们可以想象邵揶在写这首诗的时候,神情是何等肃穆。在这样的时刻,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界限全都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一切从灵魂出发又回到灵魂。人类的灵魂,这是所有的艺术之神最终必然回归的奥林波斯山。
邵揶依然在荒原上孤独地嗥叫和奔走,他不会被驯服,被招安,他的灵魂,他的作品,将永远是独立的,自由的,野性的。对此邵揶充满了自信:
上帝让我
跛着腿走路
让没听说过拜伦的少女
对我不屑一顾
上帝为我封上一扇门时
又打开一扇窗
让我实现
做大诗人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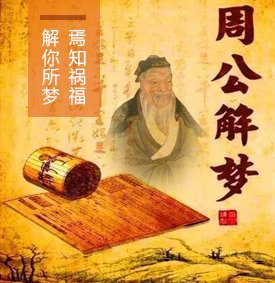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