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霁光学堂历程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年后转入历史系。1933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此后受聘为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特约纂述与编辑,并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协助主持“史学”副刊。1936年9月,离京赴津,到南开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兼任商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导师。1937年9月,随南开大学南迁长沙。
从1930年由清华大学物理系转入历史系,到因日本侵占华北而南下,这是谷霁光步入史坛并初步奠定其在中国兵制史特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兵制史研究地位的时期。而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 因素之一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谷霁光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受陈寅恪先生影响至深,“每当听陈先生讲课时,不独注意其传授知识,而是更多地注意其传授研究方法和经验。特别是陈先生当时写出关于《桃花源记》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重要论文,认真阅读后,受益大得不可估量。”
因素之二是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认可。1935年,也就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谷霁光的《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二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这一事件被视为他“步人史坛”的标志。
前一因素带来的多为兴趣,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谷霁光将他的“断代史”研究即研究时代聚焦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后一因素带来的则多为自信,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谷霁光将他的“专门史”即研究方向集中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兵制特别是府兵制度。
这一期间还有两件事情对于谷霁光日后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件事情是1934年春夏之交“中国史学研究会”的成立。1934年春象龙和吴晗等发起成立的小小‘史学研究会’,最初人数不多,第一批会员只有十人,汤象龙任总务,吴晗和罗尔纲先后任编辑,谷霁光任文书。由于这个“史学研究会”最早的成员只有十人,所以也称为十人史学小组,又因为参加者多为清华大学的青年学者,所以又称清华史学研究会,主要发起者是十人中年纪较小的汤象龙先生和吴晗先生,两人都出生于1909年,比罗尔纲先生小8岁,比谷霁光小3岁。他们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这是中国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最早的学术刊物;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办起了“史学”副刊,各出了一百多期。他们以此为阵地,相互激发、遥相呼应,发表了大量的史学论文和杂文,人人都闯下了极大的名头。谷霁光对这个群体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汤象龙、吴晗、梁方仲、罗尔纲等先生的回忆以及有关他们学术经历的文献记载,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要提到这个研究会。可见,虽然存在的时间不太长,研究会对于包括谷霁光在内的所有成员的学术生涯来说,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三十年代这段时间是他们最年轻青春的时光。汤象龙、吴晗、梁方仲、罗尔刚、谷霁光等在此期间不仅踏实认真做事,整理中国几千年积攒下的历史宝贵档案,互相之间也结下了深厚而不可磨灭的情谊,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学术上的一段佳话。他们各自在专长学术领域内树立了一座座的学术丰碑,永远值得后人仰望!罗尔刚的太平天国运动史,吴晗的明史,梁方仲的封建社会晚期与转型期的社会经济史,汤象龙的中国近代海关史,谷霁光的封建社会中期军事府兵制度,都是后来学子必看的参考数目和指导性的教材。他们的学术研究是在直接接触中国历代皇宫珍藏的珍贵历史一手的档案基础上,且都或多或少的与社会经济有所关联,带有法国年鉴学派的早期特点。
第一件事情是,1936年9月,也就是谷霁光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三年多后,离开清华,去了南开,在文学院任专任讲师,兼商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这一选择,对于谷霁光研究方向的拓展,即在进行兵制史研究的同时进行经济史研究,并将兵制史研究纳入经济史研究之中,或者说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的背景之下研究兵制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一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谷霁光日后的学术发展,离开清华、离开北京意味着离开中国的学术中心。那么,谷霁光为何弃清华而赴南开,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不见任何文献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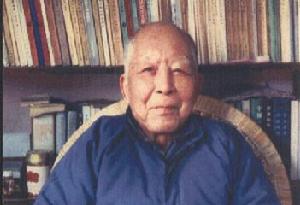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