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李青萍在荆州六十五年
2011-05-26 10:52 作者:常振威
县看守所就在县法院后面。整个监狱围着一片六、七百平方米的长方形场地而建,东面是堵高墙,墙外就是县公安局。监狱大门独占一间成两道狱门。顺狱门西三间是看守室,狱门东三间是监狱管理办公室,再东三间即女监。北面十一间、西面六间皆是男监室,监室宽约三米,深约六米,四周砖墙。前面逢中是一扇厚实的木栅门,后面老高一个小铁栅窗,下铺木地板,上是木天花板。李青萍第二次进这地方,已司空见惯,而且熟门熟路,再说也由不得她自己。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在狱中竟遇到了少小时的朋友罗传凤,此时她也关在看守所内。罗传凤家世居荆州城区,也曾外出求学,抗战时期在重庆一幼儿园谋生,与军统特务毛人凤旗下廖某成婚后,曾一度随从宋美龄左右任勤务兵,抗战胜利后辗转北京,其夫官至少将军衔,任北京战俘管教所所长;罗传凤授衔少尉,任战俘管教所女生中队长。北京和平解放前,其夫随军南撤台湾。留住北京的罗传凤在“镇反”运动时曾经被捕过,回荆州后投靠二爹,在西门外南街教私塾谋生。当年在县政协内办的“肃反”成就展览上,笔者见过罗传凤与宋美龄等合影的照片。她的“反革命罪”证据确凿,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回家扎扫帚谋生,“文革”一开始,她便被城关中学的红卫兵抓起来了,传言事起“梅花党”案,说罗传凤与李宗仁、郭德洁、王光美都有联系,被城关中学的学生乱棍打死在大北门内洋教堂的地下室里。但是,据知情人讲,“文革”之初大揪叛徒,罗传凤解放前夕在北京战俘管教所工作过,当年在狱中的变节自首者为杀人灭口,专程到荆州来谎称抓“梅花党”,才使罗传凤死于非命。
想不到两个少女时代活跃上进,成年后也曾得意扬帆,年届不惑时却遭此恶运。同囚一室,四目对视,一丝苦涩的惨笑暗示了相互的问候。狱中犯人之间是不能过从亲密的,这两个心有灵犀的知识人,仅能只言片语彼此相告境况。狱方网开一面,女犯睡木板架起的统铺,监门白天不上锁,她们可在划定的区域内行动;如出入监室上厕所等,到犯人伙房帮厨。男犯监室是锁着的,每天仅两次短暂“放风”时间,夜里就睡在地板上。相比之下,女犯是解放了。三间女监室内一共关有十多名女犯,李青萍的到来,不仅使女监的同人们瞠目结舌,就连所有男监室的犯人,也隔着栅栏门窥视;都因为她那不亢不卑的仪态,不紧不忙的神情,一身时尚的着装,处变不惊地从容。男监室的观望那只是雾里看花,女监同人的惊诧摆在眼前。李青萍早起睡前饭后都要洗漱,不穿的衣服要叠放整齐,出门理头,方便要避人等生活习惯,使那些缺少教养的山野村妇们感到失落,于是反唇奚落她:再爱干净也坐在牢里!每此,都多亏了少时好友罗传凤打圆场,她总是细言奉劝村妇们,说她是在国外养成的习惯,爱清洁少生病呀!她是个大画家,还见过周总理……最后解除矛盾的是监狱的那位女管理员。
女监不锁门,狱方安排她们洗衣服。当年,干革命的小干部多是单身,也没像现在按级别分配的住房,用机器洗衣服的事还没听说过。于是检察院、法院、公安局、还有武警队的单身们,都将衣服送到看守所来给女犯们洗,看守所也因此增加点收入;女犯们也不会太闲着而胡思乱想。一天,女管理员来到女监指着李青萍说:从今天起,她就是你们的组长,劳动、生活、学习上的事都归她安排。片刻之间,李青萍就成了女监室的狱头----“二干部”。女管理员是山东青岛人,其父南下落在荆州行署,她从老家来荆参加工作。此前在街上也见到过李青萍,入监都要登记,她多少了解点案情,指派李青萍当组长也算是对她的照顾。不然,论态度,看劳动,罗传凤绝对强过李青萍,但罗传凤历史罪证确凿,李青萍特务罪终归还只是个嫌疑。领到女管理员的旨意,李青萍只需干编号分类、收发衣服的事,凡洗涤缝补之事她只分派一声就够了,就连她穿脏了的衣服,不用言语也会有人清去洗。这就是女管理员所说的劳动、生活、学习。在狱中,说到所谓的“学习”,那尽是欺人之谈!
按监狱规定,案犯入监后就吃“皇粮”,除去衣被及洗漱用品,男犯连裤带都不准系。案件未决前,不准家属探视。家属送来的食物也会拒收。李青萍再次入狱,她母亲自然忧心,每次送牙膏、肥皂、手纸时,总要附带点瓜子、堆沙饼、龙凤喜饼等食品。那位女管理员也网开一面地转交给李青萍。自从她当上了组长,收发衣服就归她经手,只要女管理员一叫,李青萍就跑到管理室的窗口踮起脚尖接送衣服,有时,她母亲送点东西来,女管理员也有意叫她,她踮起脚尖,双手紧抓着铁栅,隔着窗口深情地看她母亲。当母亲热泪盈眶时,李青萍总是笑着叫喊她:妈,我在这里蛮好的!还当上了组长,您就别为我担忧,自己要保重啊!母亲所送的食物多是能存放的,使她每天都能补充—点,为此还闹出了—场“政治”风波:一天,李青萍将用纸包好的龙凤喜饼放在洗净的衣服上,突听管理员叫她取衣服,谁知正好要取的就是她放龙凤喜饼的这几件,管理员的呼唤就是命令。狱规上明文写着犯人要绝对服从。她匆忙抱起这堆衣服送到管理室窗口,龙凤喜饼也随衣服一起送到了取衣人的手中。那人将衣服带到办公室,放在桌上后被旁人发现有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两个荆楚名特小吃----龙凤喜饼!这事就传成了“李青萍贿赂办案人员”的故事。狱中经常突击大搜查,有次查出了李青萍“私藏瓜子”:“犯人在监狱内还悠闲自在地磕瓜子!”事发后,也被女管理员的“批评”带过。自从她当上了狱室小组长,除了管衣服登记分类和收发外,其它任何事都不用她动手了。一次审讯,预审官疑她画家是假,于是给她张纸,要她回监画张画交上去。这一来,引起她画兴大发,狱中没条件尽兴,于是她拿起筷子在墙上画。狱室的墙壁粉刷过石灰浆,虽不能说雪白,也应算干净整洁,墙壁上除按狱方规定贴有张“十大狱规”外,犯人是绝不能在墙上乱写乱画的。这事被人打了小报告,女管理员来监室一看果真,当然是一顿好训,从此不敢在墙壁上乱画。墙上不能画,她弄根扫帚条蘸水在地板上画,这事又传到了管理员那里,管理员又来制止,后来,她捡根小竹棍蘸水在狱室门前的土地上画,女管理员见了后,看看她,再看看地上,也只好摇着头离去。一次,她弄到张大点的纸,拿洗衣编号的笔在纸上画出了狱中监控犯人的“瞭望楼”,这事再不能瞒哄了,于是女管理员将“瞭望楼”交到了公安局执行股,这事也被预审官按住了,好像都知道她的“个性”。三十多年后,李青萍与那位女管理员重逢时,她赠给这位女管理员好大一幅画在三夹板上的油画。现在,这女管理员听人说其画收藏价值很高,可惜在家中再也找不着那幅画了。
李青萍再度入狱是“肃反”运动的需要;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自然要审讯她。既然说“特嫌”,也就是说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审问之事也就尽是些说不清楚的事情了:如今据审讯官回忆,羁押期间也只审讯过三四次,每次审讯官问她时,李青萍总是答非所问,审讯官问她说过毛主席是“土包子没有”?她却扯到田汉是“人贩子”,周扬是“四条汉子”上。当被审讯官逼得没有退路后,她也只说毛主席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学,从不正面承认她说过毛主席是“土包子”的话,可见李青萍也心知肚明,骂毛泽东是“土包子”,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只怪她曾漂洋过海,当年马来西亚还从属英国,从南洋归国在泰国境内,汽车因避飞机轰炸窜向海滩,被渔民救起送进医院,当时泰国与日本有外交关系,大难之时为了求生,是同伴人佯称她是汪精卫眷属才获治疗,谁知这话竟成了她的“历史”问题。视艺术为生命,论艺术无国界是她的信条,中日交战时期,她却东渡敌方去办画展(笔者认为这是她一生唯一的污点,但还构不成罪恶)。仅因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想占她几幅画作得罪了这位司令,在上海提篮桥狱中饱受了八个多月的折磨。“特嫌”、“汉奸”这些扑朔迷离的神话、嫌疑竟贻误了她三十几年。
半年之后,“历史反革命分子”罗传凤因“罪行确凿”被判刑五年。疑情莫辩的“特嫌”分子李青萍,同样被判了五年徒刑。罗传凤事实清楚,结案后即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李青萍死结难解,还是留在看守所羁押。1956年下半年全国大清案时,正直的办案人出于良心,对李青萍案提出了质疑,李青萍才不明不白地走出了狱门,又才回到江陵县文化馆“工作”。李青萍晚年与办案人重逢后,还念念不忘办案人当年的开通,并特聘这老先生为她的法律顾问。
炼狱归来,李青萍只能一声不吭地面对生活了,可是到“整风反右”后期,她又因“一言不发、对抗运动”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一言不发”也成了罪过!至此,李青萍头上戴了“汉奸、特嫌”和“右派分子”三顶帽子。不久便被集中押送到湖北大冶铁矿去改造,名曰“劳动教养”。劳动教养的实质是非常荒唐的,与其说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不如说它还不如劳动改造;劳改犯还有限期,劳动教养在当年是无期限的,有的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在劳教农场一干就是二十几年。说到工资更是欺人之谈,每月不超过二十元钱,扣除伙食,余下的钱难够日常开销,若说到被褥、蚊帐、四季衣服,还不如劳改犯的“供给制”踏实。劳动量和劳改犯一模一样,受限制的程度也同劳改犯相差无几。李青萍到大冶时,正值疯狂的全民“大办钢铁”之际。待这场热症消退了后,她们又被发配到咸宁赵桥茶场修地球。其间适逢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正常社会的人们都饥肠辘辘,划地为狱的囚徒可想而知。该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被埋葬在那片土地上!李青萍的命硬,所以才没有葬身在那片茶园。
1961年底,年届50岁,更加弱不禁风的李青萍拖着疲惫的身心被遣散回原籍荆州城。回家了,且不说母女重逢的悲欢离合,首要的难题便是无处安身!1958年,当她被押往大冶不久,荆州城区又搞了一场“大革命”,这次革命的名目是对私有住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简称“私房改造”。一夜之间,成千上万幢房产都归白手起家的镇房管所了。李青萍家那点祖辈传下来的私房被“改造”后,仅给她母亲曹庆珍留下了不足20平米的“自留房”。就在李青萍无可奈何之际,胞弟李先成也从地缝钻回来了。李先成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1949年考入华东军政大学,后分配到交通部南京公路勘测设计三院工作,职务是桥梁工程师。“反右”之时在劫难逃,也被送到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了四年多,也是这次“大赦天下”时被遣散回原籍荆州的。李先成的不期而至,更使母亲曹庆珍悲喜交集。此时—家三口,一男二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也只有挤在这不足二十平米的方寸之地栖身了。
俗话说:人生在世,也就是“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姐弟两未回家时,母亲曹庆珍仅靠私房被改造所谓“定息”及儿子赵毓贵供养。摆在眼前的大事,姐弟两一日三餐,总不能去喝西北风吧?李青萍找到文化馆,别人说:你以为自己是国家干部,原本就是个临时工,又劳动改造了几年,我们这样的单位还会要你这样的人吗?李青萍自己也懵了!临时工还参加“大鸣大放”?但是,这道理又能找谁去讲呢。李先成硬着头皮去了几次劳动局,最后总算将他安排到与他原工作还很对口的县交通局工程队做合同工。上班后,承情交通局领导们安排他同—班人专事收购砖渣的工作。说起这砖渣,当年在荆州城内,就像如今各地都开采小煤窑一样,真似个挖之不竭,取之不尽的一大宝藏,以前就有人靠挖残墙断壁卖整砖为生者,现在碎砖也派上了用场,先是用它拌三合土垫房基,后来慢慢发展到维修公路。历经两千多年兴衰的古城,仅这些残垣断壁就曾养活过多少穷途末路的被困英雄!李青萍就曾是这支“拣砖渣团队”的一员。李先成带上一班人成天在城区的大街小巷内收购砖渣,这本来是一件太容易不过的工作。可是这老先生遇事太认真了,硬是要交通局印制些规范的收据、表册,一时间又将人员分工为收尺、制票、复核等。按理,如此是理顺了工作头绪,既可避免收砖渣中出现差错,又能防范作弊行为,但这一来工效就低了。于是有人认为:一个右派分子,成天抱着个文件夹指手画脚的,叫人看到后多不顺眼!再加上他又“不思悔改”,南京城隍北京土地的成天乱侃,1964年2月12日是农历大年除夕,是晚,全工程队人员聚餐,就在聚餐会上,工程队的王英队长,举起酒碗给李先成敬酒时对他说:根据交通局的指示,你被解除了劳动合同!这就是对他说,从此刻起,李先成已不是工程队的合同工了。旧社会时的雇员最怕年末聚餐被老板请到上席坐,因为一经被请到上席,就表明你已被辞退了。可那是旧社会的事。那年月不存在什么劳动安排,更没有什么合同工制度,全凭老板一句话。再说,当年受雇的人东方不亮西方亮,张老板不雇你,可以去找李老板,而现在找工作非得通过劳动局。交通局对劳动局招呼也没打,一脚就将李先成踢走了,叫他又怎样去劳动局再要求安排工作呢?王队长的话使欢快的聚餐会顿时变得一片死寂。李先成听了这话,抬手将碗里的酒一饮而尽。喝完了酒,他闭上双眼,仰面朝天停顿了片刻。他想了想年近八旬的母亲、与他风雨同舟的姐姐、唯一还在他身边的女儿,突地发出一声悠长的惨笑后说:“好!今天是大年夜,能聚在一起也不容易,来点高兴的,我给大家唱段戏,也算是向王队长叫辞罢。”于是他清了清嗓子,唱起了: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架上鸡,惊醒了,梦里南柯……后来大家才知道,李先成原来是在交通部第三设计院工作的,而且是桥梁工程师。可能见他年岁太大,加上爱管闲事,所以将他打发走了事。有人背后议论说,若不因为他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恐怕你这小小的江陵县打轿子将他也抬不来。
此时,江陵县工程队创建之初,由劳动局安排来的人,除少数几个小青年外,尽是些在历次运动中受过打击的人。所以,在交通系统内流传着汽车队是“小台湾”、工程队是“劳改队”之说。原由是汽车队是由马车队发展壮大的,马车队的大多数人是解放前夕从河南逃亡到江陵县的,故云汽车队是“小台湾”。也因工程队中有李先成及笔者之类的一批人,曾经在劳改农场呆过,或是头上还戴着“四类分子”帽子,所以被称为“劳改队”。此时我也是县工程队的一名合同工,所以目睹了王英如此对待李先成。1958年,年仅十六岁的我还是名初中学生,被荆州中学将我和我的八位同学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我也历经了四年多的炼狱之灾,和李青萍、李先成遭遇同时。因此,对李先成此刻的处境倍感同情。因为我原来就认识李青萍,春节期间,我大胆地走进了李青萍的家,给她和李先成拜年。当时他们还住在故居,走过房屋二重的封火墙,过天井进堂房右手就是他们的住房,—家四口(李先成长女李正璧已到荆州),祖孙三代,都住在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房子里,李青萍见到我这个不速之客,心中有些惊讶,在那隔墙有耳的年代,我们都不敢深谈。几句问候后,我小声问她还画画吗?她望着我神秘的微笑后,不声不响地从床头的破棉絮下翻出几张三十二开大小的画来给我看,只见些废纸片上被那斑斓的色彩泼洒得流光溢彩,五彩缤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青萍的泼彩画,我虽看不出这些图画的意境,仅这鲜艳夺目的色彩、自然流畅的笔触,就令我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她说:捡破烂时能拾到装过广告颜料的瓶子,这是用瓶子中所剩的颜料脚子画的。看完后她很快就收起来,又压到床头的破垫絮下了。我也不便久留,于是向她和她母亲告辞。
李先成被划右派后,为了不影响两个女儿的前途,只得与妻子分手,是李青萍不忍目睹她弟弟家败人散的局面,从劳改农场回家不久,她专程到武汉,将在卫校读书的李先成的大女儿李正璧接到荆州。李先成被工程队解雇后,从此便开始了他浪迹人海的岁月。到处做泥瓦小工,挖土方,挖下水道……再怎样“革命”,他脑子里那些工程技术的知识总革不掉。因此,他成了“盲流”、打工者们的“狗头军师”:揽到活路要他造预算,开工价,谈施工条件等,直至结算、分配,都归他一个人来干。因此,直到他去世,还有好些曾和他一起“盲流”过的人在他身边走动。自从李先成失去工作后,这对右派姐弟的生活就更是步履维艰了。李青萍不知找街道多少次,街道干部们才将她侄女李正璧安排到城关环卫所去扫大街。为了生存,李青萍也不能在家里干坐,先是求人说情,在家街道幼儿院帮助老师看小朋友,街道主任知道了,这还了得!这样的人也能去教幼儿园?那家幼儿园的老师知道了,只好请她回家。临时工也不准她做,最后想到了捡破烂。从此,她左手提着个破篮子,右手持把火钳,终日奔走在垃圾成堆的地方。城区内年过五旬的人都曾见到过一个身材瘦小、,背近佝偻的老太婆,经常穿双左右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鸳鸯”鞋,踽踽独行在垃圾堆中,那就是李青萍。若是李先成收工了还不见姐姐归来,就拿上破口袋往各处的垃圾堆去找她。找到了,将她拣到后堆存在一起的破布废纸装进破口袋,姐弟俩才背着、提着,踏着暮色返回。此时李正璧总守在煤炉边煮饭,老眼昏花的母亲总站在门框边静守。等回李青萍、李先成,母亲才—声长叹地蹒跚进屋。—家四口才围着张锯掉靠背的木座椅,母亲坐在床弦上,李青萍坐个小板凳,李先成坐块城台砖,李正璧就倚着门框,在一盏十五支光灯泡的照射下,一盆水煮罗卜,—盘腌咸菜。李先成呷口酒,举起筷子在咸菜中拌几下后送到嘴里,然后就闭上双眼,谁也不知道他是困了,或是在想着什么。一口饭在李青萍口里要嚼好久,她总是口在嚼着,头在不住地转动;看一眼抖动双手握住碗筷的母亲,看一眼双目紧闭仰面朝天的弟弟,再看一眼亭亭玉立倚着门框边的侄女。老宅的墙壁几近赭色,破烂的铺垫一片土黄,室内没一件东西能在灯光的照射下回光返射。每到此时,斗室内静极了,在那昏暗灯光的影照中,瘦骨嶙峋的四个人真像皮影在摇晃。就像当年时兴吃“忆苦饭”的氛围。每此,那场景严肃得几近阴森。除了碗筷的碰撞声,晚餐总是静悄悄的,长年如此。
当年,人们都生活在煎熬之中,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凭证供应,一件衣服补了又补,买牙膏不仅凭票,还要交空牙膏皮,连白菜萝卜都曾凭票供应过,哪能像如今,只要能吃苦,能放下“身架”,一天捡到的废品少说也能换回十元八元的,绝对不亚于吃“低保”。到了夏天,李青萍又“死皮赖脸”地去找居委会写证明,到食品厂领棒冰去沿街叫卖。李先成求他“地下包工队”的木匠做了口木箱,拿出床破棉絮将箱内几面密闭起来,又弄块干净布在表面—钉上,再衬张油纸,棒冰箱就拾掇好了。每天绝早,李青萍背上大木箱到食品厂去站队,等人家上班后,批上三五盒棒冰后就去沿街叫卖。卖棒冰就盼天热,要的就是酷日当头。只有如此,家长才满足小孩的欲望,才有生意。李青萍沿街叫喊着棒冰,“棒冰!香蕉棒冰!绿豆棒冰!”一支棒冰的利润才六厘钱,一天要卖出近两百支才能赚一块钱。卖棒冰最怕阴天,特别是刮大风,空气对流快,棒冰就容易化。唐代诗人白居易《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每当正午,李青萍这苦命人:可怜满身汗涔涔,心忧棒冰思酷热----再热些就好!李青萍身材矮小,沉重的棒冰箱挂在肩上,毒日当头负重叫卖,本来就嗓音嘶哑,那声声叫卖真似杜鹃滴血般的凄楚。若遇天凉风大,不到下午,未卖出去的棒冰就会融化成水了。于是,化成的甜水就是李青萍的晚餐。所以,直到李青萍八十多岁,还情有独钟地爱吃棒冰,她怎能忘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啊!
后来,街道办起了小工厂,专做化验粪便的小纸盒。街道干部见李青萍会画画,于是安排她进这小工厂去画线打样。样打好了,下料切角是机械操作的,街道工厂既没钱,又没计划,买不起电动机,于是用人力摇动大转轮代替电动机。在这街办工厂里,谁都比李青萍年轻,谁的体质都比李青萍强。可是,街道主任却非要安排她来摇大转轮。也有好心人向街道主任说情,那主任却说:“这事该‘五类分子’去做!”
来源: 共识网读者吴长青荐稿 | 责任编辑:袁训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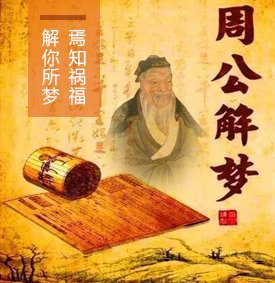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