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带走了另一片风景
大约是在2003年,我和温州作家程绍国先生坐在雁荡山之大龙湫边上喝雁荡云雾,说起林斤澜。程绍国先生当时正在写《林斤澜说》,每写一段,就去北京找林斤澜先生交谈,然后再回到温州续写之。在中国文坛中,有着林斤澜先生与程绍国先生这样的友情,在生前就约好慢慢述说并写传,我以为程绍国先生挺有幸的,因为在北京这个大文学圈子,以短篇小说和文字取胜的作家,莫过于汪增祺与林斤澜了。而汪增祺先生已经过世,短篇大师里面,剩下林斤澜先生独自行走。
我较早读林斤澜先生的短篇,应是林斤澜先生创作之巅峰时期写的系列《矮凳桥风景》,这个系列陆续发了许多篇,后来结集。林斤澜先生较少参加文学圈的活动,我去闯北京以前,他担任过《北京文学》主编,这方面已经有许多的文章介绍,林斤澜先生籍主编之位,发现了不少的青年作家,现在这些人都是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比如余华。但是,我仍有机会在一些活动中遇到林斤澜先生,以《北京文学》构成的文学圈,相应来说都比较质朴与厚道。我在浩然任主编和章德宁任主编时期,也发过一些小说。问题是,我了解林斤澜先生,还是在程绍国先生那里。
林斤澜先生一生都喜欢温州的鱼生,这所谓的鱼生,它是温州人的专好,用小带鱼和萝卜丝混合盐腌,加红曲,它是生的,外人难以吃出其妙处。据说温州人把它带往海外,欧美国家海关的检测警报往往响起,拿去检测,细菌超标300万倍,海关检查官问做什么用(人家以为是毒品吧),温州人说是吃的,检查官就如见到外星人:这也能吃?啊,这也能吃?温州人再带鱼生去海外,就包数层塑料袋,不让海关检测仪测到。
林斤澜爱吃鱼生,北京买不到,只有从温州带,程绍国先生就每每带着鱼生上路,到了北京,品着鱼生的林斤澜先生,就很高兴地跟程绍国先生谈,这么谈出一本《林斤澜传》,并已于前年出版。也是因为这个原故,我才知道林斤澜先生是温州人而不是北京人。
一个热爱乡土与美食的人,我感觉到林斤澜先生的可爱与可敬,唯其如此,其落笔于故乡之时,方有得那颤若游丝般的精细与独到。然而,想不到林斤澜先生就这么走了,他的走与汪增祺先生不同,汪增祺先生在辞世之前,有些个小小辉煌,在文坛颇为热闹。林斤澜先生则不同,他始终处于低调的生活,北京喧闹杂乱的大酱缸文坛,鲜有他的身影。唯知道“林系”作家子弟兵们,皆以文字精美为己任,不复有糙。如程绍国、瞿伟等温州作家,文字婉约清新,又都默默耕耘于世。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悖论,谁个的文字愈是精美而行事低调,就受不到公众视野关照,谁个浮躁之极,文字傻大粗黑,倒一直是聚焦中心,不过对于作家,终究还是要籍文字传世罢,如此说,倒是林斤澜可以有些许慰籍,毕竟留下诸此精品短篇,未曾入糙。
古清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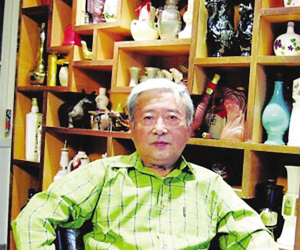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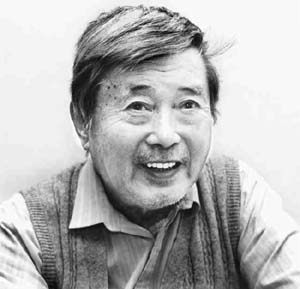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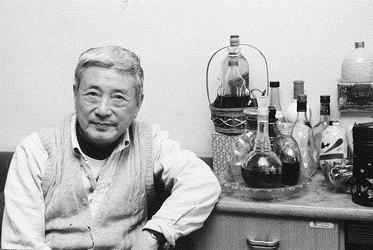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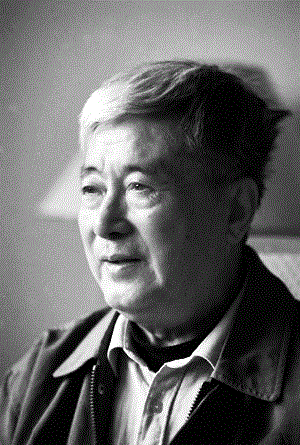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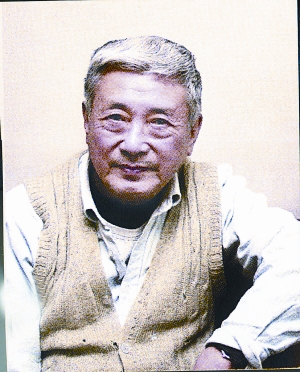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