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邓拓
1961年秋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晚报》做副刊工作时,马南邨的《燕山夜话》专栏文章已经连续刊登近半年了。到了副刊“五色土”,我才得知《燕山夜话》作者署名“马南邨”,是当时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的笔名。我在人大新闻系读书时,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曾给我们讲过课。我当时就觉得他知识渊博,对文、史、哲都有研究,尤其对近代、现代新闻史相当熟悉,对他顿生敬佩之情。
到副刊不久,晚报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顾行,有一天对我说:“邓拓同志想到京郊西山看看,你也去吧。”我承蒙关爱,欣然前往。那天秋高气爽,满山红叶。我坐在司机旁边,邓拓和顾行坐在后面。汽车绕过颐和园的昆明湖,奔驰在玉泉山下结满柿子的峡谷里。每遇碑碣、寺庙、古迹的废墟,车子便停下来。邓拓、顾行走向碑石,研读碑文;或看残宅前的石雕,赞美古代石匠的手艺。看到游客在红墙、石柱、古树上胡乱刻画着“××到此一游”,邓拓叮嘱顾行在晚报上写杂文批评这种破坏文物的恶劣现象。在一个古建筑废墟上,邓拓弯下颀长的身子,捡起一块黄琉璃瓦片,对顾行说:“琉璃瓦古称缥瓦,唐宋时就出现了。唐代诗人皮日休、宋代学者王子韶,都在他们的诗文里提到过。封建贵族除琉璃瓦外,还盖过铁瓦、铜瓦、银瓦,但老百姓只能在房顶上铺砖瓦、石板甚至稻草。可见即使一块瓦片,如果对它做深入研究,都有很多学问。”我听着邓拓一席话,顿觉郊游变成了一堂历史课。
在晚报工作了几年,我知道邓拓对书法、诗词、绘画、文物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他用钢笔竖写的每一篇“夜话”,都可以说是一幅珍贵的书法作品,令我爱不释手。他的行书潇洒俊逸,笔势舒展,气韵丰沛,有行云流水之感。他常以“友海”为笔名,给我们副刊发表的速写、国画配诗。我见过他送给福建友人的一幅山水画,笔墨疏朗,意境高远,是典型的文人画。
邓拓的《燕山夜话》,谈政策、时事、科学、史地、文艺、书法、动植物,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无所不谈。我记得他写过一篇《围田的教训》的文章,说:围田“势必使湖泊河川的水面缩小,一旦洪水暴发,被缩小了的湖泊河川更容易泛滥”。早在四十多年前,他就富有预见地告诫人们不要砍伐森林,不可围湖造田,山秃了,湖小了,必然引发严重的自然灾害。
邓拓的记忆力好,知识广博,写一两千字的专栏文章,常常一挥而就,倚马可待。写到后来,邓拓发动大家给他出题目。我们从读者来信中发现了合适的题目,就用电话告诉他。邓拓得到了题目,不用两个小时,就叫通讯员把稿子送来了。
当时每天都有全国各地大批读者来信涌到编辑部,表示爱看《燕山夜话》。有的读者来信评价《燕山夜话》“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知识丰富,文笔流畅”。老舍称《燕山夜话》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不拘一格”。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说《燕山夜话》“既有思想性,又有知识性,学富五车的人才能写得如此精彩”。后来全国许多报纸,如《大众日报》、《云南日报》等都仿效《北京晚报》开了杂文专栏。《燕山夜话》的影响,当时波及到了大江南北。
1963年,文痞姚文元曾写信给出版《燕山夜话》合集的负责人,对《燕山夜话》大大地赞美一番,说它是“北方难得的思想之花,希望北京出版社也像对待《燕山夜话》那样,出版一本我的杂文集”。可是到了1966年5月初,他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昧着良心抛出一篇批判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说《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江青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胡说邓拓在《燕山夜话》中“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1966年5月1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诬说邓拓在历史上是叛徒,矛头指向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
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党内才子邓拓写了他的申辩,给亲人留下了遗嘱,于1966年5月17日深夜含冤离世。
张守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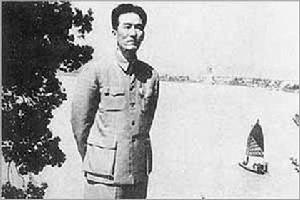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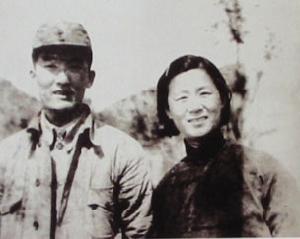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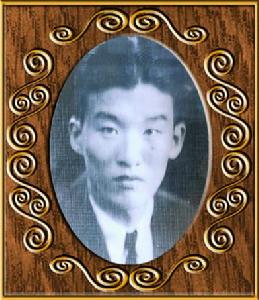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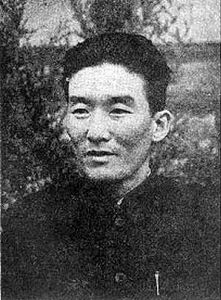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