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丹心——百岁老人谢孝思的传奇人生
【人物档案】
谢孝思,别名仲谋,1905年农历八月廿七日生于贵阳,著名书画家、党外民主人士。
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系,师从国画大师汪采白、吕凤子。上世纪30年代,任贵阳市达德学校校长,与著名爱国人士黄齐生先生一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起,先后在重庆正则艺专、国立艺专、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授。1946年随社会教育学院迁居苏州。
解放后,先后任苏州市文教局局长兼园林修整委员会主任、苏州市文管会主任,为苏州园林及古城保护等建言奔走,不遗余力。历任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政协副主席、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州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民进江苏省委副主委、民进苏州市主委等职,现任民进苏州市委名誉主委、苏州市文联名誉主席。
题记
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人,历经沧桑巨变。我看到过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腐败、没落,更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开明和进步。对我这样一位性格比较执着,思想比较活跃的人,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指引和关心,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党非常关心我、信任我,我也十分热爱党、信赖党。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深感幸运和自豪。―――谢孝思
许多传奇都是在执着中书写而成。谢孝思的故事也不例外。这位已然度过了百岁寿辰的老人,在一个世纪的人生路上,心怀知识分子的良知,执着地追寻光明和进步;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执着地与共产党人风雨同舟。曾经的种种磨难几乎毁灭了他,但他的执着却历久弥新,痴心不改。谢孝思就像山顶的一株青松,周身不乏火烙印痕,却始终滋生着坚不可摧、奋进向上的力量。正是因为这种执着和忠诚,老人跨越一个世纪写就的传奇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肃然起敬,依然是那么绚丽精彩。
两度逃亡,黑暗中追寻光明的方向
1905年秋,谢孝思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大南门外一个衰落的书香世家。5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全靠母亲栽树种菜操持度日。尽管家境清苦,6岁时,母亲仍坚持把小孝思送进了当地一间私塾。私馆发蒙,间读初小,12岁进“正谊高小”,14岁考入“达德学校”,天资聪慧的谢孝思在如饥似渴的学习中长成了翩翩少年。
当时的达德学校提倡新文化运动。学校的创办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先生积极组织师生学习接受新思想,并选送师生留日、赴法勤工俭学。王若飞作为该校的校友,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经常写信回校,宣传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令师生们耳目一新。达德的光荣历史和浓厚的民主校风让在此求学的谢孝思深受其益。1923年,谢孝思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并被黄齐生先生收为入室弟子。
达德学校因“开创贵阳新风气”而饮誉贵州,同时也引起了统治当局的严重不安。1926年,军阀周西成以“结党营私,图谋不轨,勾结共产党人捣乱贵州”为名,强行解散了达德学校。追随黄齐生先生的谢孝思也因此成为“危险分子”而失业。苦闷和失望之余,谢孝思决意离开贵州,投奔黄埔军校。于是,他剃成光头,假扮和尚逃离了警戒森严的贵阳。在东进的路上,他收到了家兄“从文不从武”的千字血书,旋即转道南京,考入中央大学美术教育系,师从吕凤子专攻美术,走上了艺术之路。1932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谢孝思回到了贵阳,被推选为达德学校校长。彼时,“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贵阳成立了教职员抗日救国会。被推举为总干事的谢孝思竭力投入到募捐款物和宣传抗日的工作中。而国民党贵州当局为了消灭共产党,大肆造谣惑众,称“共产党抗日不积极,团结无诚意”等等,一时间人心惶惶。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谢孝思商请黄齐生亲赴延安找王若飞问明情况,并毅然变卖了部分房产作黄的路费。
黄齐生到达延安后,党中央以贵宾之礼相待。在延安参观考察了半年之久,毛主席称他为“我党最困难时候,同情共产党的第一人”。黄齐生回贵阳后,带来的所见所闻令谢孝思兴奋无比。经过认真商议,谢孝思随老师黄齐生开始在校内校外频繁演讲,介绍延安新气象、宣传共产党真心抗日,使许多贵阳人了解了真相,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
这下又触怒了当局。不久,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下令通缉黄齐生。为了防止不测,谢孝思随同黄齐生、偕他的侄孙黄晓庄逃离贵州,直奔昆明。旅程中,他们三人还不忘进行抗战宣传鼓动工作。在沿途停留之时,谢孝思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黄齐生就延安见闻进行演讲,黄晓庄则教唱《大刀进行曲》,俨然是一个抗日救亡队,在群众的欢迎中谢孝思感到了前进的力量。
这次旅程中的一件小事至今让谢孝思记忆犹新。一天,走到一座山的半山腰,天近傍晚,山雾浓浓,谢孝思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禁吟诗一首:“一天风露湿衣裳,始觉他乡异我乡。四面空谁慰得?虫声唧唧桂花香。”谁知,黄齐生听了这首诗,却狠狠地批评起谢孝思来:“我们这样奔走,不是落魄潦倒没前途,而是为了抗日、为国家、为民族振兴尽我们的一份义务。”黄齐生义无返顾的精神和肺腑之言深深震撼着谢孝思的心灵,他认错了。从此,先生“追求光明不畏艰难”的教诲在谢孝思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1942年,应恩师吕凤子先生之聘,谢孝思来到重庆正则艺专任教。期间,他推荐黄齐生来正则艺专任教授。出于对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由衷钦佩,每年谢孝思都会主动征集百余幅师生的书画作品,由黄齐生交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转送延安以示慰问。在重庆,谢孝思还有机会与王若飞等一批共产党人相识相知。王若飞等共产党人渊博的学识、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念、博大的胸怀和高风亮节,无不令谢孝思折服。通过他们,谢孝思确信自己找到了光明的方向,追随中国共产党成了他终身的心愿。
多年以后,回顾已走过的人生历程,谢孝思为自己深感幸运。他说,正是由于早年幸遇黄齐生、王若飞等一批革命先辈,得到了他们的谆谆教诲,才练就了自己耿直的品性,以及对党、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也正是因为这种信念历经了磨砺,当“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造反派轮番批斗之时,谢孝思虽有丝丝心灵的伤痛,但始终没有放弃对光明的追随和信任,以不可动摇的意志最终迎来了人生又一个春天。
心系古城,倾力文化保护的日日夜夜
1946年,一所名为社会教育学院的大学迁到了苏州。该校教授谢孝思也成为了古城苏州的新居民。落户之后,贵阳人谢孝思发现自己这辈子也不可能离开这里了。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有着2500年历史的古城,自然条件优越,人文景观丰富,有着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保护好苏州名城和文化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该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
可是,混乱的时局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1948年,在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院长企图随同国民党迁走学校。谢孝思立即团结进步教师,迅速与苏州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组织全校师生成立了护校委员会,日夜巡视学校,同贪污的院长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院长无奈,只身潜逃。谢孝思还组织了院务委员会,积极保护了学校设施,以迎接苏州的解放。千年古城回到了人民手中。谢孝思为终于有机会能以学识报国而欣喜异常。果然,苏州解放后不久,新成立的人民政府领导找到了谢孝思,诚恳征求开展苏州工作的意见。当时,苏州城百废待兴。看到没有文物管理机构,文物流失严重的状况,谢孝思建议成立一个不挂牌子、不要编制、只要一枚公章、配备三名临时工作人员的“苏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市领导欣然同意。谢孝思毛遂自荐任文管会主任。时间不长,经文管会抢救、搜集、捐赠的文物就达8000件,珍贵图书资料5万余册。
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要继承和发扬,首要的条件是必须充分认识它们的自身价值和丰富内涵。1953年后,谢孝思任苏州市文教局局长,市委领导让他主持园林整修委员会工作。他便倾注精力,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聪明才智,先后对拙政园、留园、狮子林、虎丘、沧浪亭、怡园、双塔以及万寿宫、寒山寺、玄妙观等古典园林和寺庙进行了整修,恢复了它们原来的面貌。其中,由他主持的留园修复工程成为他平生一大快事。修复前,该园墙断壁残,荒芜不堪,谢孝思与同事们广泛征求意见,制定计划,与工人同吃同住进行修缮,仅用半年多时间,花了5.3万元,就将这座大型园林修复一新,并为此后其他园林的整修积累了宝贵经验,使该园林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市第一批开放的园林,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使全国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艺术重放异彩,针对解放前从艺人员分散、缺乏统一组织和专门研究的情况,谢孝思力主成立了刺绣研究所等机构,并邀请乱针绣的发明者杨守玉和她的两个高徒任娴、周巽先,对有关从艺人员进行现场指导。任娴更创造了双面异色异样绣法,为刺绣这个苏州最美丽的艺术再添新彩。
“从1952年开始以后的三四年间,我在苏州的主要工作是文化建设方面,特别是园林修整,现在保留下来的苏州园林和一些名胜古迹,基本上都是我所经手的,这是我对苏州最大的成绩,也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事。”在总结这段人生经历时,谢孝思曾经这样自豪地说。
参政议政,真言善策方显忠贞本色
1949年苏州城解放,谢孝思的政治生涯也因此迎来了春天。从1949年底苏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协商委员会,谢孝思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起,他一直以文艺和民进等界别代表身份参加政协,并担任市政协领导职务,直至1993年市八届政协期满。参加政协后,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把广大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人士紧紧团结在共产党周围,风雨同舟,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直是谢孝思所思考和尽职努力的工作。
解放初期的苏州有一大批像周瘦鹃这样的社会贤达,他们很少过问世事,过着闲散的隐居生活。有一次,市领导找到谢孝思了解情况。谢向他反映了苏州许多社会名流赋闲在家的情况。市领导听后郑重叮嘱谢孝思要很好地宣传党的政策,积极动员他们关心和参加苏州地方建设。此后,经过谢孝思的反复努力,终于把周瘦鹃、萧退隐、潘昌煦等邀请“出山”,又动员了范烟桥、蒋吟秋、程小青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政协学习和有关活动。这些人为弘扬苏州的优秀文化、培养造就人才尽了一份力,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充分肯定。谢孝思因此也获得了“拖拉机”的雅号。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的重要职责。在长期担任民进苏州市委主任委员期间,谢孝思以“肝胆相照”自励,团结民进会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心同德地与中共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带领会员深入实际,了解基层,积极为苏州的建设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了参政党的作用。
谢孝思常说,当好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很不容易,既要建真言,又要献善策。真言善策要成为党政部门的共识,也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那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精神,对每一位政协委员来说,显得弥足珍贵。
谢孝思自己就有这样的例子。苏州这座古城在敌伪时期遭受长期破坏。解放后,城内又办了一些很不适宜的工厂。到“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大拆城墙,为此许多有识之士颇感担忧。出于一种责任感,时任市政协副主席的谢孝思,力陈保护古城墙和全面保护苏州古城的观点,几乎是遇领导必说,逢会必讲,并在市政协会上作了《正视苏州特色,明确苏州性质,才能很好地建设新苏州》的专题发言。但那毕竟是民主法制极不健全的年代,他的意见非但未被采纳,反而被攻击为反党言论。谢孝思因此被一度免去了市政协副主席职务。但他并不为此感到可惜。赋闲的日子里,谢孝思一面整理被抄家失散的文化资料,一面还在暗自思忖着古城保护的课题。
“文革”一结束,谢孝思把全面保护苏州古城风貌问题列入了民进苏州市委参政议政的重点。1983年,经过周密考察,形成了《为把苏州建设成美丽的风景旅游城市而努力献计献策》的调查报告。1984年,在市政协七届二次全会上,谢孝思作了《谈谈我对苏州城市性质的认识》的大会发言。同年,他在省政协五届二次全会上,提出《紧急制止对苏州文物古迹、园林名胜破坏》的提案,并以民进省委副主委、民进苏州市委主委的身份,通过民进中央将该提案转交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1986年,国务院颁发了《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为全面保护苏州古城风貌提供了依据。看到这份批复,谢孝思欣慰地笑了。
(摘自苏州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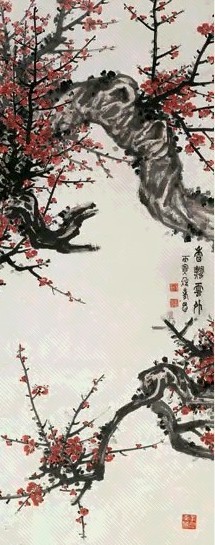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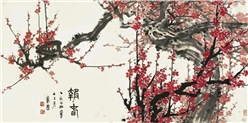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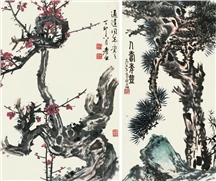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