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帆:革命书生夏征农
他是海上文坛的活跃作家,他是参与南昌起义的热血青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是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他出过书,打过仗,坐过牢,做过学问,当过大官,吃过大苦。他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
他是夏征农。生命的长度、韧度、广度和深度,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2008年10月4日11时16分,夏征农走完了他105年的人生路。
【文学时代】
“夏征农”其实是个笔名。
他原名夏正和,字子美,出生在江西新建县(现封城县)一个地主家庭。在夏正和给自己取“征农”这一笔名的时候,他年轻的生命中已经发生了许多大事:他在21岁那年离开家乡,到南京金陵大学念书;他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回江西迎接北伐军队,参与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他在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到上海,经同乡罗汝谋的介绍认识了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成为一名复旦学子。
就是在复旦,夏正和爱上了文学创作,并给自己起了“征农”这一笔名。现在看来,这两个字竟然“一语成谶”:他漫漫一生的革命征程,从描写农民生活的文学作品开始,在对“三农”问题的殷勤关切中结束。
年轻的夏征农喜欢文学,但绝不是吟风弄月的闲散文人。1929年,他因从事地下工作而被捕,一关就是两年。坐牢期间,他曾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被转移到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那次的行程被他写成一篇《从上海到苏州——别有风味的游记》。文中,人们丝毫读不出沮丧或恐惧,只能看到一个年轻的革命者身上特有的乐观、坚强、甚至天真:“我们每人一首提着一个大包裹——因为只有一只手可用,另一只手已和别人的拷在一起了,虽然吃力,却尚有余勇可贾似地异常兴奋……”
出狱后,夏征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短篇小说《禾场上》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受到了该杂志主编茅盾的注意。茅盾指出,《禾场上》的作者“并没意识到要写革命的农村小说,只把农村中收获的一幕老老实实地写了出来,然而农民被剥削的实况却已经表现得非常生动了”。名家的表扬让夏征农大受鼓舞,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写了《春天的故事》《结算》《萧姑庄》等十几篇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这些作品为他在海上文坛赢得了名声,让他成为“左联”的主要成员。
1934年,夏征农担任他的恩师陈望道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编辑,由此结识了他一生敬仰的人物——鲁迅。《太白》上几乎每期都有鲁迅的文章,其中“掂斤簸两”栏目发表了鲁迅《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名人与名言》、《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等名篇。夏征农当时和鲁迅经常通信;鲁迅逝世后,夏征农约请几个朋友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文集。
【戎马生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地下党员夏征农收到一项特殊的任务。
1937年初,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经国在苏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初回国时的政治理念上与其父甚为不合。蒋介石对这个儿子也没什么办法,只好把他派到赣南当一个保安处长。蒋经国在赣南组织了“江西青年服务团”,网罗了一批文化人,如何士德、孙席珍、程懋筠等。夏征农便在那个时候到了赣南,身上背负着“统战”蒋经国的任务。
在赣南,夏征农的身份是“高级参谋”。据他日后与儿女们的回忆,蒋经国对他很尊敬,称呼他为“夏老师”。从1937年10月起,他在蒋经国身边工作了大约一年的时间。1938年秋,时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找到蒋经国,指出夏征农是共产党员,应该逮捕。蒋经国于是请夏征农吃了一顿晚饭,席间说:“你不能再呆下去了,否则我控制不了了。”并且赠送钢笔手枪一把,一来给夏征农防身,二来请他留作纪念。夏征农当夜逃走。几个月后,蒋经国正式主政赣南。
这段故事,从未见于正史,是夏老的子女在此次采访中无意聊起的。记者于是问,夏老为什么从未在讲话或文章中提及此事,儿子夏晓华说,他父亲觉得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自己的那段历史(那支钢笔手枪后来在战争岁月中丢失),索性就不说了。
与之类似的是,夏征农没有写过回忆录,连“口授实录”都不愿意。他的一生认识那么多的人,遭遇过那么大的事,本人的文笔又好,但就是不愿把那些过往记录下来。夏征农晚年曾对他的儿女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应该由历史和人民来评价、而不应该由自己来吹嘘。当然那已是后话了。
时间回到1941年的秋天。“皖南事变”后,夏征农被分配到苏中任苏中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根据夏征农本人在文章中的说法,那只是一个虚设的机构,实际他就是军区司令粟裕的秘书。在夏征农的回忆中,战场下的粟裕为人谦虚,甚至有些腼腆,有客人来都不愿意见。平时不谈自己的战功,也不议论别人,生活作风朴素至极。夏征农非常佩服粟裕,因此虽然自己的年纪要大几岁,但心甘情愿当粟裕的助手。
2001年,“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逝世。当时已届百岁高龄的夏征农特意写了一篇悼文,将粟裕称为“战争时代与我相处的日子最久、关系最好”的同志。
【蹉跎岁月】
“文革”十年,而夏征农蹉跎了十二年。
如果单看1961到1965年间夏征农的作为,很难看出他会在未来岁月中倒大霉。自61年11月被调到中共华东局任宣传部部长之后,夏征农连续三年发起华东六省一市现代戏话剧汇演、戏曲汇演和京剧汇演。这些汇演涌现出后来成为“样板戏”的《龙江颂》《奇袭白虎团》《沙家浜》等剧目,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然而夏征农却得罪了江青。江青在上海搞样板戏的时候,夏征农当众顶撞她说:“我们只能搞半成品,搞好后再给你去搞成样板戏吧。”1966年的5月,夏征农被免职,接替他职务的人是张春桥。
其实夏征农耿直、不会说话、容易得罪人的个性,早在解放初期就初露端倪。1958年,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他因为“反右不力”的罪名被免去职务,下放到莱芜县任城关东社书记。他不急着委屈叫屈,倒亲自搞了一个炼钢炉。当发现一两铁也炼不出来后,便向省委报告说:“你们不要再要求每天放卫星了,所有的卫星都是假的!”旁边有人看不下去,说他实在不识时务,已经受了那么大的处分,还像没事人一样。许多年以后,夏征农谈及此事还会哑然失笑,说自己确实有些“书生意气”。
“文革”开始后,夏征农先是在外被“游斗”两年,1968年2月回到上海,作为“中央重点专案”被关进“隔离室”。最初的时候,囚禁的地点是位于康平路上的荣毅仁旧宅。那里距离夏征农的家仅一街之隔,而他碰巧住在面向街道的一个亭子间里。他虽然无法和家人通话,但时不时会向路面上丢一些从火柴盒上撕下来的小纸片。某一天,他的儿子们终于发现了纸片背后的秘密——那是父亲在隔离室写的诗歌。
比如,1968年1月10日,他们的父亲曾用鲁迅《无题》(“惯于长夜”)一诗的原韵做诗:
那堪长夜过春时,隔绝尘寰两鬓丝。
梦里犹惊查“黑线”,心头但怕失红旗。
低眉自问非蛇鬼,侧耳人歌动地诗。
四顾囚居余寂寂,路灯一线照军衣。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夏征农与其他11个“重点专案”被转移到少教所,家人从此失去他的音讯。直到又过了两年,夏征农才从“隔离室”里放出来。他进家门时的那一幕场景,深深地印在他的儿子夏晓鲁的记忆中。
“他所有的衣服都是白的,都是洗白的,”夏晓鲁向记者回忆道,“他带着满满一大网线袋的书,都是马恩列斯的著作。”
人虽然放出来了,但身份地位并没有恢复。夏征农先是到奉献“五七”干校劳动,后又到“红九连”(即今天的上海社科院所在地)学习。每一天,都要读文件、写检查,直到1978年。
【主编《辞海》】
平反来得非常迅速。1978年7月之后,夏征农被接连任命为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顾委委员。那一年,他74岁。
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杨心培带话给他,建议他“安个帽子”、恢复名誉就行了,那么大年纪,别出来工作了。而夏征农的回应是:他只要工作,至于职务、名誉倒无所谓。
夏征农当时对妻子方尼说,我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十二年,只好在今后工作中努力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只是那个时候的他恐怕也想不到,他即将做成那样一件大事。那件事不仅将成为他本人一生的巅峰,也将让他成为古今中外的一个传奇。
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既是领导、可以调动资源,又有学识、懂得尊重学者的夏征农,成为《辞海》主编的最佳人选。于是,明朝的解缙39岁编纂《永乐大典》,清朝的纪昀49岁编纂《四库全书》,而夏征农从74岁起执《辞海》编纂之牛耳。
夏征农走马上任的时候,距离出书时间不足一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部1300万字大辞典的编纂出版工作,谈何容易!而最困难的还不是时间,而是“指导思想”。《辞海》副主编巢峰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政治背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起草,中共十一大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赞扬“文革”,推行“两个凡是”路线,但与此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引起广泛共鸣。《辞海》该如何解决那些疑难杂症?比如,阶级斗争怎么写?路线斗争怎么写?“文化大革命”怎么写?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林彪、康生等怎么写?孔子、海瑞、李秀成等历史人物又怎么写?
为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夏征农派主持常务工作的罗竹风专程去北京请示。罗竹风在北京盘桓二十多日,找了二十多位领导,但得不到答复。巢峰只好自己起草了《<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八条十九款,对“阶级斗争”等敏感词条一一提出具体的、在当时情况下异常大胆的处理原则。罗竹风、巢峰聚在夏征农的家中,对《意见》逐条研究,由夏征农一一拍板定稿。巢峰清晰地记得夏征农当时说的话:“我是主编,要我负责,我就敢于负责;如果要我定,我也敢定。”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最终,1979年版的《辞海》成为一部基本上尊重历史和事实的辞书。比如,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专条中,只讲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以及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并且不作评价。
1981年,夏征农提出《辞海》应“每十年修订一次”,得到批准。那之后,由他主持编纂的1989年版和1999年版《辞海》相继出版。有人以为夏征农也就是挂个虚名而已,其实不然。一些重大问题还是由他拍板、出面;只要《辞海》开工作会议,他都参加。
在1996-2004年间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的李伟国告诉记者,在编纂1999年版《辞海》的那几年,他每个月都要去夏老家好几次,每次说上20多分钟。让李伟国印象深刻的是,夏老一点都不唠叨,不会像一些老人家那样一有机会就说个不停,你问问题,他清晰地回答你,言简意赅。
“可惜夏老看不到2009年版的《辞海》了,这也是由他主编的。”李伟国略带伤感地说。而巢峰向记者透露,明年9月将出版的《辞海》,将增补收入“夏征农”这一条目。
【百岁之后】
2004年1月31日,夏征农的百岁生日。他高兴地赋诗一首,为自己祝寿:
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
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
根据巢峰的回忆,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有人向夏征农请教长寿秘诀,夏老说:“我什么病都得过,什么苦都受过,只是死不掉而已!”当时全场大笑。
事实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夏征农在耄耋之年获得了令人钦羡不已的幸福。仿佛是老天看到了他一生的磨砺和精诚的意志,最终将“福”与“寿”都一股脑儿地给了他:他在百岁之后仍然身体康健、神思清晰,并且五代同堂,子子孙孙竟超过一百人。
和许多长寿老人一样,夏征农在晚年时分返老还童,呈现出孩子般的天真烂漫。“爷爷真是好可爱的,”夏老的一个孙媳妇向记者回忆,“他看到我出现在门口,就会说,‘是不是又给我带粉蒸肉来啦?’脸上笑得那个开心噢!”
然而他毕竟不是普通的百岁老人。夏征农最后几年的护理小祝告诉记者,夏老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那就是看天气预报——不但要看上海地区的,还要看全国范围的,因为“爷爷担心有旱灾、水灾什么的,怕农民受苦”。夏征农的最后一任秘书钦浩补充道,夏征农在晚年最挂念的就是农民。胡锦涛、习近平、贺国强等中央领导来看望他,每一次,他谈的都是“三农问题”。
夏征农的健康状况是在一年前出现问题的。夏晓华告诉记者,去年下半年,他父亲听说自己是“十七大”的特邀代表,非常兴奋,成天考虑到时要讲些什么,怎么谈好“三农”问题。老人知道大会开幕前要齐唱《国际歌》和《国歌》,还很认真地学唱。不仅如此,他担心自己走的步子太小、走在队伍里会妨碍拖累别人,便成天在过道里练习“大步走的要领”。
然而,医生在为夏老检查身体后发现,老人的心脏早搏较多,便建议他不要上北京了。毕竟,夏老当时已是104的老人,医生的担心绝非多余。然而夏老却很不开心,觉得自己人生最后一个心愿无法实现,并很快就一病不起:先是肺炎,随后是心脏衰弱,最终的死亡原因是胆结石引起的胆管堵塞。
上海华东医院院长俞卓伟告诉记者,住在医院南楼303室的夏老,是那个病区里“最安静的病人”,“没有要求的病人”。
其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夏征农也曾提出过“要求”,只是那注定不会实现。那两条要求是:“一,要是实在不行就不要治了,不要浪费国家的钱;第二,我活了那么大岁数,死后最好让医生们解剖一下、研究一下,看看为什么能活那么长,如果研究出了什么,还能给人民做点贡献。”
夏老逝去之后,俞院长在带领医护人员向老人告别时,禁不住走上前,拥抱了老人的遗体,并在老人的额头上印下一吻。
夏老的家人没有过分的哭号,因为夏老生前反复叮嘱:“不要哭得太大声,以免影响其他病人的情绪。”
有谁能复制这样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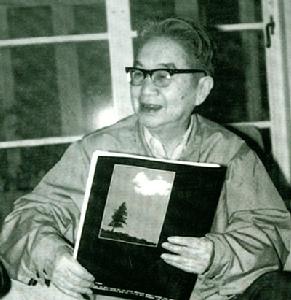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