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我是个真理探索者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集体照(1962年),前排左起第二人为卓炯。
卓炯率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卓炯
1908年1月24日生于湖南慈利,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61年冬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1987年6月24日,卓炯因呼吸道疾病于广州病逝。
生平
1928年,在湖南常德中学念高中时,因思想进步被怀疑而入狱。193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6年广东学海书院研究生肄业。
1939年,卓炯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1946年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受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启发钻研《资本论》。1946年出走泰国,任曼谷南洋中学校长,兼任中共党支部书记。1949年3月,任云南人民反蒋自卫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卓炯历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
如果意见完全一致,就用不着再讨论了,我是个真理的探索者,既然是探索,就不能认为自己说的都对。学术上,某些重大问题的探讨需要时间,不必急于作出结论。———卓炯
“卓老这个人”,81岁高龄的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曾牧野老人侧过头冥思了一会,时光流转,思绪俨然回到了半个世纪前。
1961年即提出计划商品经济理论
1959年,曾牧野参与广东省经济学会筹建,认识了卓炯等经济学界前辈,此后相处28年,曾老将卓炯称作良师益友,“卓老比我年长整20岁,我刚进研究所时就知道他了,他提出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后,在省内乃至国内都有很大反响,我们也很受震动,开始比较多地关注、了解他的理论。”
1961年,卓炯在《中国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下,无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流通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曾在《光明日报》上指出,卓炯是我国第一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学者。当时经济学界有个流行的说法,“北有孙冶方,南有卓炯。”
曾牧野强调说,卓炯有这样的远见先行绝非偶然,“上世纪60年代,他在广东省内多家报刊发表文章时都用了‘于凤村’这个笔名,为什么叫这个呢?”曾老说,“1960年到1961年我们都参与了‘整风团’,他去肇庆下边的德庆县,还挂了县委副书记的职,蹲点的地方就叫凤村。”
这段经历使卓炯亲身体会到“大跃进”运动包括关闭农贸市场、否定商品经济的极左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他为什么要写关于商品经济的文章?是因为在凤村工作的那段时间,受到了实践的启发。过去不让搞商品生产,农民生活苦得很,怨声载道;可是当党采取措施纠正了错误以后,农民很高兴,政策对头,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就把农村的经济面貌改过来了。这段经历,对他影响非常大”,曾老回忆说。
同时,卓炯从40年代接触《资本论》后开始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直到离世也未停歇,还留下了几十万字相关遗作。据曾老介绍,逝世前几年,卓炯还试图借鉴《资本论》体系,改造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以商品经济学为特色的新体系。
对做官的事没兴趣
1979年秋,广东省委下文,落实文革前已决定的任命,同意卓炯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副所长。时任研究所领导的孙孺将此事告知卓炯,他只是莞尔一笑,表示接受省委的决定,但又立即说:搞行政,我没经验,行政工作让孙孺同志还有老廖(廖建祥)多管,我多搞点学术。
老友仿佛又在眼前晃动,曾牧野笑了,“他是个老实人,淳朴、平易近人,对做官的事没兴趣。当了副所长后,所里说要给他换办公室,他说不用搞这些了。事实上,他也没怎么管过行政工作,那几年全在钻研学术。”
淡泊名利,卓炯对学术却异常执著,曾老由此回忆起几件往事。1979年,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写了本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据曾老回忆,起初的稿子还有点社会科学的味道,后来经修改却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调靠拢,引起争议。卓炯和孙孺、赵冬垠等一起,坚决反对小册子的基调,认为讲社会主义不谈经济问题没有道理,从此这份书稿被否定。早在1962年,卓炯就曾对几位同事感慨地说,“我们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可是容不得知识分子多说几句话。”曾老说,此话含意深刻、尖锐。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证明了卓炯的高瞻远嘱,使他载誉于决策层和学术界。卓老在倍感欣慰的同时,并不以此为傲。直至改革开放后,仍有不少人对卓炯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卓老不以为意地回答,“如果意见完全一致,就用不着再讨论了,我是个真理的探索者,既然是探索,就不能认为自己说的都对。学术上,某些重大问题的探讨需要时间,不必急于作出结论。”
年近八十仍阅改青年学者习作
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李江帆至今仍常回忆起第一次去旁听卓老讲课时的情景,“我第一次见到卓老应该是在1980年3月11日。那时候,卓老已经72岁了,同时被聘为华南师院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兼职教授。为了‘先睹为快’,华南师院79级6个研究生抽空一起到中大旁听了卓老的《资本论》应用课———《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
作为新人,听课前李江帆已不止一次地听师长们谈及卓炯独树一帜的“商品万岁论”和“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论”,以及他在极左路线的高压和打击下毫不畏缩的种种传闻。面前站在讲坛上的则是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慈祥长者,李江帆至今仍保留着当时的课堂笔记。
不久,年轻的李江帆撰写了论文《略谈物质生产劳动者日趋减少问题》,求助专业杂志编委无果后,想到了卓老,投出信后又颇感心里没底,卓老热情的回信很快打消了这些想法。李江帆至今仍由衷感叹,是卓炯的热情与提携助他走上了关于第三产业的研究之路,并确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
据上世纪80年代的媒体报道,1986年第一季度,年近80高龄的卓炯阅改来自全国各地青年学者的习作就达50多万字。
1987年6月15日上午,卓老应邀前往刚成立的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参加答辩会。当时在场的丁家树教授回忆说,卓老在答辩会上一边听,一边打瞌睡,甚至发出了轻轻的呼噜声。他当时想,卓老真是太老了,3个小时的答辩会对这位79岁的老人来说已是负担,以后再也不能请他老人家来参加答辩会了。
不料一语成谶,9天后的6月24日,刚参加完孙孺追悼会的人们一回到家就听闻噩耗,之前因感冒引发心肺疾病的卓老在医院骤然离世。
在卓老逝世9天前,助手杨永华请卓老到他家里吃午饭,杨永华一家三口住的是一间又黑又闷的小房,仅12平方米,连厨房也没有,要在走廊做饭。尽管如此,卓老那天仍旧显得很高兴。他对杨永华说,现在房子太小,等你以后搬了新房,我们再好好地做一顿饭,把其他几位老师也请来聚聚。住处与杨的宿舍仅十几步路远的李江帆错过了这顿饭,却不曾想,就此与卓老诀别。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俊彦
本版图片: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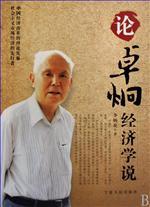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