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民族感情
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这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只说“在外地工作”。但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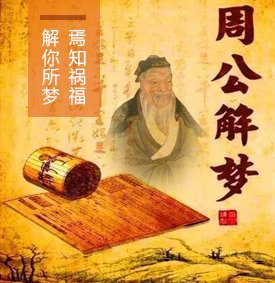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