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清明,怀念岳父
又到清明,怀念岳父
松针簌簌抖落山雾,青石台阶上苔痕愈发明艳。我扶着碑沿洒扫时,忽见石缝里钻出簇簇紫堇——像极了他蘸着油漆补渔船时,袖口溅落的点点星辰。三十年前他教我辨认山径的清晨,总把最鲜嫩的清明菜塞进我的竹篓,自己啃着冷硬的玉米饼子,说硌牙的粮食才经得起风浪。
老槐树下斑驳的条凳还记得他泡茶的模样。搪瓷缸里的野茶永远浮着松针,他偏说这才是"山水真味"。暮春夜雨涨满池塘时,他带我蹲守芦苇丛,手电筒光柱里跃起的银鲫总先放进我的鱼篓。有次我失足滑进泥潭,他解下棉袄裹住瑟瑟发抖的我,背风处燃起的篝火舔舐着寒夜,却将他鬓角的白霜镀成金箔。
工具棚里木香犹在,刨花堆中躺着未完工的桃木剑。孙女出生的那年,他戴着老花镜打磨了整宿,说要把山神的祝福刻进每道纹路。化疗期间仍偷偷给邻村孩子修陀螺,颤抖的手握不住凿子,却能用青筋暴起的手背稳稳托住旋转的童年。
清明火纸旋成灰蝶的刹那,山风卷来熟悉的烟丝味。他生前最爱的铜烟锅躺在檀木匣里,匣底压着张泛黄的字条:"给姑爷备着,山雨湿气重"。去年霜降我翻出他补过的蓑衣,霉斑间忽然滚出几粒板栗——该是某次巡山归来,他藏在褶皱里的秋天。
半山腰的野樱开得正酣,粉白花瓣落满他开垦的荒地。我摘下斗笠接住纷扬的花雨,恍惚听见他中气十足的吆喝从云端传来:"接着!"怀中襁褓突然咯咯笑出声,婴孩瞳仁里跃动的光斑,多像他当年指着银河说"那是先人提着灯笼走亲戚"时,眼底闪烁的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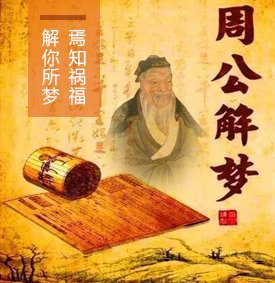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