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荃麟的悲情人生
一、理论家邵荃麟——为底层人民的命运和神圣权利呼喊
半个多世纪前,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从旧书铺买到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文光书店1947年第二版)。读了以后,正如译者在《译后记》中说的那样,使我的灵魂为之战栗和震撼。我不仅从此对这位俄国作家有了一些认识,还记住了译者荃麟的名字。他于1943年写的《译后记》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有些内容至今不忘。他说,他是在病中翻译这部书的。生病读陀氏的书,本就极不适宜。读了又放不下,常常激动得连夜不能入睡。他为它战栗,为它流泪,情绪极度沸腾时以致被迫搁笔而无法继续译述。他还说,他对这本书“有特别的爱好”,因为它描写了“人性在极度的凌虐下和残酷迫害下一种绝望的几乎是疯狂的反抗心理——他那种从社会底层发出来的愤怒和热情的声音是使世界震栗了,在19世纪40年代的人道主义运动中,杜思退益夫斯基的声音无疑是最杰出的——”这些分析和评语,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译者一定也是一位忧郁伤感的人,有强烈人道主义同情心的人。
以后,我又有机会读到荃麟更多的文章,发现他对文学作品描写底层人物的命运特别关注。面对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他极力主张作家不要为那些表面上煌煌惊人但却肤浅皮相的所谓重大题材所迷惑,而是应该踏踏实实地“伸入到黑土的深处”,“和人民共命运”,“去感受同样的痛苦和愤怒”;“这需要有正视伤痕的勇气,有刮骨疗毒那种忍受力,这需要剔除一切脓疮的瘀血,需要肃清血液中一切封建和法西斯的细菌……”这些基本精神相似的论述,分别见于他在40年代前半期所写的《向深处挖掘》、《伸向黑土深处》、《我们需要“深”与“广”》等论文。这些论述与他对陀氏小说的感动和体验完全是一致的,即关注、表达在苦难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底层”的生活命运。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的作家也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在这同时期,他写的一些研究评论作品的文章,同样阐释了这些思想观点。如他写的关于阿Q的系列文章,特别强调了鲁迅创作阿Q的深刻的典型性,不仅仅在于阿Q与阿Q主义具有世界性、现代性的普遍意义,最重要的是通过阿Q写出了中国底层人民的奴隶特性,“奴隶的失败主义”,但又“是在反叛着”;写出了奴隶的“根性”、“弱点”、“精神病状”。他说:“阿Q的历史是中国低层的愚昧无知的人民被压迫的一幅史图。”(《也谈阿Q》)愚昧无知原是世界上最悲痛最残酷的事情,鲁迅是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直面残酷的人生,“替当时中国人民画下了一幅最真实的史图”,而这正是他的深刻之处。“这是多么锐利的笔力啊,世界上是否有(其他)艺术家,曾经写出比这更令人战栗的性格么?”(《关于〈阿Q正传〉》)试想想,二十年后发生的“文革”,所以能够裹胁全国苍生于其中,不与此有关吗?
荃麟在许多评论文章中,都不遗余力地发挥、讲述这个基本观点,如他热情推荐当时还不知名的青年作家路翎的新作《饥饿的郭素娥》,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就是因为它“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许)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和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荃麟在他的前期著译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真诚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构成了他的思想核心。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爱心,不是廉价的肤浅的居高临下的怜悯,也不是仅仅停留在良心和道德的感性层次上。因为他深刻认识到这不是具体的个别人的命运问题,而是一个人类历史的问题;他表述的呼喊的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应有的生活和幸福的神圣权利和要求,他憎恨和诅咒的是那些侮辱和损害别人的统治阶级。邵荃麟的革命生涯和文艺写作历程都是从此开始的。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低层人民不幸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以后,邵荃麟的生活和写作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下文中还会比较详细讲到。但是,邵荃麟的基本思想并没有从他心底消失。所以,当五六十年代之交,大跃进失败带来空前的灾难,严重的饥荒遍及全国,(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多达四千万左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就如已故老作家陈登科生前亲口告诉我的那样:“那时我们安徽(饿)死人不是一个二个,而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饿)死去的……”因此,1962年大连会议上,赵树理在讲述农村恶化了的可怕形势后,激动地说:“1960年简直是天聋地哑!”诗人方冰接着说:“是天怒人怨!”作家们的激愤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从生活实际中引发来的,忍无可忍的反应。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百姓正在遭受着如此深重的灾难和痛苦,能不触动邵荃麟,能不引起他深思、战栗和震撼吗?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希望作家们在这个会上,深入地研究文学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他强调要看到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粉饰现实,回避矛盾,不可能是现实主义”。他说,“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又一次引用了自己在1945年写的《伸向黑土深处》中的思想:“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现实。”他肯定了人们在会上一致赞扬赵树理的创作,因为在大刮浮夸造假风之时,只有赵树理坚持说真话,表达了农民的真实呼声。所以荃麟说:“这说明老赵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优秀的理论家,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位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家,一定是忧人民之所忧,和人民共命运同呼吸。他决不会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这是邵荃麟一生所追求的、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于是,在当时有限的言论空间,他自己讲,也推动别人讲出反映底层人民苦难生话的真话,尽管还是比较委婉曲折的表述,但已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了。这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也是它的伟大之处。
二、革命家邵荃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
但是,邵荃麟还不只是一位作家理论家。他最主要的身份是职业革命家,后来是高级文化官员。
1926年,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邵荃麟,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从此终身从事革命,始终不辍。他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选择,正是由于要求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底层人民的神圣权利。这与他上述译著中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信念。他从一开始就怀着满腔热情,曾参加了有名的上海工人武装暴动。虽说是书生一员,却英勇地参加了街垒战。后来,他一直在江浙一带基层,做地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被选为去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后因病未成行)。如果沿着这条革命之路发展,无疑他将是一位专门从事政治革命以至武装革命的资深的杰出的职业革命家。
意外的是,在他参加革命二三年后,染患了严重的肺结核。那时的肺结核在人们眼中是一种可怕的绝症。他只得暂时养病多年,一方面继续关心革命,一方面却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量阅读文学著作,从事写作小说剧本理论文章。当他健康情况恢复较好,重新工作时,虽然他仍是一位秘密的职业革命家,但从此有相当时间是在文化艺术出版等领域里活动,并且是以一位有影响的文化人、作家、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种双重身份一直保持延续在他一生。
但是,对邵荃麟而言,他首先是忠诚坚定的革命者,在秘密地下状态,冒着生命危险,不屈不挠,始终把党的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而文学事业,只是第二位,是服从和从属于革命需要的。他信奉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日常工作中,也贯穿在文学写作中。那时他写的作品文章,是按他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加以具体化了的。在地下党的环境中,一般没有太多的干涉。所以,在三四十年代,政治革命家的邵荃麟和革命文艺家的邵荃麟,两者似乎配合互补,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
在这个地下时期,邵荃麟先后主要在浙江、桂林、香港等地活动,已是党在文化界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解放初期,他在国务院文委任副秘书长,主持或参与了扫盲、创办工农速中、建立公费医疗制度、少数民族地区根绝性病计划等等诸如此类造福万民的开创性的大事。因此,如果评估他前期的工作实践和文学写作两个方面,可以说像古人所要求的那样,既立功、又立言,都有大成。
但是,1953年后,他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主要领导(先后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任党组副书记、书记),情况有了变化。固然,他在文学界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写了一些评论新作的文章,尤其对青年作家的扶植培养爱护,是众所周知的。但就他的写作而言,诸如一些重要的文章:如第二次文学工作者(作家)代表大会的总结发言、《文学十年历程》、批判胡风等,基本上是作为党的发言人,努力阐释党的文艺政策,说服作家按党的政策来写作。这些论述,都是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甚至日丹诺夫那里寻找论据,再加上级领导的意图和斯事斯地的政策要求,混合而成,很难辨别出多少是他自己独立思考的成果。这些文字,作为当代文学史料自有它的价值;若从文学理论角度去推敲,其中机械唯物论、教条主义、绝对唯政治化的倾向,还是相当突出的。这与当时整个政治环境和他的“发言人”身份直接有关,这不只是邵荃麟个人的问题。但是,作为理论家曾经有过的闪光的独立的思辨,人们却不太能感觉到了。
在实际工作中,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把每个人都裹挟进去,在文学界又更加频繁而严重。从反胡风斗争,反“丁陈反党集团”斗争,反右派斗争……,邵荃麟都是以党组领导(先是副书记,后是正书记)身份,贯彻上级意图,或参与或主持,程度不等,尽管力求表达自己的一些不同意见,但都无济于事,也脱不了干系。因此,我们发现他在这时的“功”和“言”都出了问题,值得进一步反思。
现在我们没有发现他在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如日记、书信等,不知道他那时的实际思想状况究竟如何?因此只能试着从几个方面的当事人的反映来作一些推断。譬如,先从几位被批判者的反映来看,对他似乎不仅没有特别反感,反倒比较理解、宽容。反胡风时,他也写了长篇批判文章,是从理论上进行批驳的,也有某些恶言相加,这是所有大批判不可缺少的惯用的词语。但是胡风在“文革”后写的回忆录中却说:过去在上海、桂林时,“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和他在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胡风回忆录》第285页)从现有的资料看,整个作协的反胡风斗争是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的领导下进行的,接着的肃反运动具体领导机构即“五人小组”组长也是刘白羽。其间很少有关邵的言行记录,他因病不怎么参与。所以胡风的回忆所述,虽指过去历史情况,但也说明他对邵荃麟的基本看法是一贯的。
1955年反“丁陈反党集团”时,邵在青岛养病,直至1957年初回北京上班,因此没有介入此事,得以全身而未沾(连)。1956年,对丁陈问题进行重新甄别时,邵“经过深思熟虑、极其慎重”地表态支持为丁陈平反,并认为“丁玲是一位卓越的革命作家,他一向很敬重,说她‘反党’显然不能成立……又强调文艺界应加强团结,过火的斗争,误伤同志,这一惨痛教训应汲取”。(见丁宁:《忠诚与屈辱》)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形势骤变。中宣部长陆定一多次召见几位作协领导,当面一再强调:“有一股右的潮流,十分猖獗”;“丁陈是歪风的代表”,对“丁陈斗争要继续”,“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荃麟竟被人发现似乎“有些折中,态度不鲜明”。他仍然“还是非常强调实事求是”。(见《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112、116、128页)直至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央对文艺界指示“驳倒右派,斗争要狠”后,他才开始转向;至于心里是怎么想的,无人知晓。到了后期,处理丁玲时,他代表党组与丁玲谈话说:政协小组会讨论过,丁玲“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和写作,稍微降低或保留原工资……”丁玲听了,“的确心动了,如果真能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心事总算可以了结——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的权威人士的恩准吗?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见丁玲:《风雪人间》第196页)果然,最后的结局是“撤消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这与邵的善意宽容的设想完全是两回事。这也正是丁玲已经预见到了的。因为丁玲知道邵的与人为善的方案是难以为另一些人接受的。
同样,在丁玲丈夫陈明的印象中,“邵荃麟没有延安整风那一套东西,整丁玲没有张牙舞爪,比较善良,很多领导人不愿见右派,他见了丁玲,还谈了全国政协会议情况,并好心建议丁玲下乡时改一个名字”。(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124页)
这些情况都说明邵荃麟在那时的党组成员中,是个异数。他与周扬们的意见不同但又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他对革命内部残酷斗争不以为然,但又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自己与党站在一起;他的地位虽高,有了比较温和的意见却还是不得不屈从于顺风顺势的同僚们极端的战斗性,于是就违心地勉强跟随着当时阶级斗争潮流走。他对冯雪峰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一例。
说起邵荃麟与冯雪峰的关系,却是非同一般。1939年邵任地下东南局文委书记时,曾帮助冯雪峰恢复党的组织关系。之前冯因与党内意见不合,回乡下老家,丢掉了关系。1943年,冯从上饶集中营逃出来到桂林找邵,又是邵向周恩来报告后帮冯恢复关系,并送冯去重庆。这样的患难之交,如今上级决定在批斗丁陈以后,开展对冯雪峰的斗争,使邵处在极端尴尬的困境。关于邵的反应,也有二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邵荃麟在批判丁陈会上的发言(1957年8月13日),原想避而不谈冯的问题。但周扬却要邵把批冯的内容加进去。(见李向东、王增如:《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第227页)邵不得不谈,但仍还尽量避重就轻,还不忘叙述冯过去的光荣历史。据说周扬、刘白羽都不满意;一说,那天“荃麟发言,重点批判冯雪峰,气不喘,汗不流,一气讲了两个小时”。(见丁宁:《忠诚与屈辱》)郭小川当日日记:说荃麟发言,对“雪峰这一部分讲得特别精彩”。(《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158页)无论哪一种说法,反正邵荃麟在那次会上批判了冯雪峰。至于是真心诚意认为冯是反党分子,还是违心伤害同志,我们不得而知。据说,反右派斗争后,冯雪峰仍然是邵荃麟家中的座上客。邵一点不避讳,不怕沾连。(见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31页)由此可以推想,邵的真实思想是怎样的了!
上述是那些被整挨批的当事人的反映。这里再介绍几位得到过邵荃麟帮助的当事人的反映。老作家黄秋耘在解放前就曾在邵领导下工作多年。50年代又在中国作协共事,又是上下级关系。黄在1957年已被中宣部点名批判,面临被打成右派的绝境,是邵“力保”(同前第184页)过关,免去灾难。毕竟以邵的地位,保个把小人物还是可以的,但还是有点风险,那些被斗争火焰煽动起来的群众对此就提了许多激烈的批评意见。黄秋耘还说,反右以后,邵对一些右派作家的处境很关心,经常向黄问及,如邵燕祥、王蒙等,说“他们是很有才华的作家和诗人”(同前第131页)。在黄秋耘的眼中:“邵荃麟是一个正直的人,处处都以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不过,我总觉得在他身上的文人习气相当浓厚,温文尔雅——像他这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领导人,我一生中遇到的并不太多。”(同前第128页)黄秋耘再三强调说,邵荃麟为人一贯宽厚,与人为善;对于作家作品,尤其如此。
曾经在地下时期一起战斗过的老作家聂绀弩,是这样评说邵荃麟的:“其为人也,口无恶声,胸有成竹,急人之急,损己利人。”(同前第127页)
曾经一起工作,受过帮助的老作家艾芜说:“我同他认识多年,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或者怒形于色。每次和他相见,总觉得是个朋友,或者同志,而不觉得是个领导,顶头上司。这主要决定于他对人的态度。他不只是平易近人,而且和蔼可亲,人们愿意和他谈心,或者表示不同意见。”(《悼邵荃麟同志》,见《文艺报》1979年第4期)
另外一位党外作家巴金,在1958年毛泽东号召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大规模批判老知识分子,姚文元与中国青年杂志就联手发动批判巴金,形成一个时间长达半年多,部分报刊、青年学生集体围攻之势。邵荃麟先后多次过问此事,当然也是得到周扬支持的,所属文艺报刊不参与这场批判。他与巴金长谈,叫巴金不要紧张,也不要勉强做检讨,把巴金已经写了的有检讨内容的《巴金选集•后记》从出版社撤回。巴金在“文革”后回忆说:“荃麟同志当时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我心里想着一个朋友(指邵荃麟)。在姚文元一伙人围攻我的时候,他安慰过我。……他为了说服我同意抽去后记,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新版《选集》中又采用那篇后记,不仅是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纪念这位敬爱的亡友。”(见巴金:《随想录•怀念非英兄》)
当然也有些人另有看法。如前所述,在陆定一明确表示要对丁陈再一次展开斗争后,刘白羽就对郭小川“谈了好一阵荃麟的缺点”,认为,“荃麟有些折中,态度不鲜明”。(见《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116页)郭小川也有同感。郭最初就是因为陆定一赏识他“有战斗力”,才调他到作协任秘书长,后任副书记。郭对邵荃麟,从一开始共事,就嫌他说话啰嗦,“不够鲜明有力”,(同前第40页)另一位中宣部领导林默涵也嫌他“一讲就是几小时”。其实,都是嫌他战斗性不强的意思。9月16日批丁陈总结大会,周扬发言即为后来毛泽东欣赏并修改的题为《文艺战线一场大辩论》这篇名文。那天作为党组书记的邵也发了言,郭小川很是不满,觉得“讲得太长了,真急人……”。林默涵对“荃麟的耽误时间大有意见”。(同前第180—181页)试想与周扬的发言比较,邵当然相形见绌,大大逊色,不够有劲了。至于周扬对邵持什么看法,也无从查考。但到60年代初,据说周扬在与郭小川谈话时,几次说:“荃麟可以少做工作,你和白羽能干,多做工作”。“荃麟年纪大了,身体很坏,以后白羽、文井和你多做一些工作……”(参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221、223页)当时荃麟约55岁左右,长周扬二岁,至于身体确实非常病弱。
看来,对邵的反映固然因人而异,但却殊途同归,都是说明:邵荃麟在作协这段时间,在频繁激烈的阶级斗争暴风雨中,“功”、“言”乏善可陈,远不如以前的革命业绩。倒是在斗争的反复曲折过程中,以他的一贯的人道主义同情心,还尽可能给一些处境不幸的同志以帮助,用温和的与人为善的言行解人之困。哪怕最后并不成功,但总还是作了最大的努力,尽了他的心意。因此,在“立德”方面却显示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高尚的人格和良知,因而为人称道。须知在那个年月,要做到这点是大不易的。就像韦君宜在《思痛录》里说的那句名言:“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见《思痛录》第51页)其言之沉痛,发人深思。
我在60年代初曾见到过这位可敬的领导同志。一次在作协会议室,一次在大雅宝胡同邵府。后者是在晚上。作协有关的几位领导都参加了。内容是讨论《中国文学》的办刊方针。如很多人描写过的那样,他是那么瘦弱,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制服,真的是弱不胜衣的样子。他是老肺病患者,不知为什么抽烟却很多。因为我也曾患过肺病,知道这是很禁忌的。他在会上很少说话;说了,声音也很温和,毫无在场有的人那样难免有些革命的高调。我的印象里,他善良亲切但又有一点忧郁的样子。然后,等到下一次见到他时,是在1966年秋,“文革”腥风正烈之时,在展览馆剧场,人们批斗田汉、阳翰笙、林默涵、邵荃麟四人,都穿着一样的灰色制服即变相的“囚服”,剃了光头,揪出来低头站立在台前示众,接受种种羞辱和批判。且不说别的人,就说邵荃麟,像他那样一生信奉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的领导及其事业怀着绝对的忠诚,对组织绝对的服从,几乎可说是“朝乾夕惕,忠于厥职”,但又是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时时把底层人民的命运放在首位的革命者、知识分子,在那样的体制统治下,是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的!
三、苦恼的邵荃麟——我“干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
今天,在纪念邵荃麟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无论从缅怀,还是研究的角度,都不能不对大连会议和所谓“中间人物”论的问题作一次更深入的探讨。因为事关对他的理解和认识。我在1978年底写过一篇评述文章(刊载于《文艺报》1979年第3期),现在看来当然是很肤浅的,但明确了几个基本问题:一、大连会议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会,而是一次革命文学工作者研究文学创作如何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会议;二、“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不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黑理论,而是文艺工作者对文艺创作的一种正当的探讨;三、1964年以《文艺报》编辑部名义写的批判荃麟的文章,引述的大量所谓荃麟的观点、言论、罪状都是假想的,强加的,凭空虚构的,不能成立的。我是在查阅核对了大连会议全部原始记录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关于这篇文章的内容,不在这里重复赘说。只想介绍一些写作和发表过程中的有关情况,有助了解事实真相。1978年底,在文学界平反冤案开始之时,我向《文艺报》主编冯牧提出邵荃麟的问题,当即得到支持,并命我执笔。文章写完后,冯牧深知此事的复杂性,故极慎重,将初稿送编委会传阅并讨论。这大概是《文艺报》复刊后唯一的一次编委会。会上,林默涵同志说:说邵荃麟同志是叛徒这个历史问题,应该实事求是给予平反。关于中间人物论问题,邵荃麟同志明明是说过的。大连会议后,周立波到我这里说:现在好了,路子宽了,可以写中间人物了。这是事实。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如果荃麟没有说过,那就应该平反。现在是确实说了,那就不能平反。刘白羽同志在会上则说,文章要集中火力批判“四人帮”,不要涉及1964年《文艺报》的批判文章。散会后,他对冯牧又特别叮嘱一番。冯牧转告我,我说,不说1964年的批判,就说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不清冤案的真相。冯牧只得说:尽量淡化一些吧!文章发表后,林默涵在一些场合作报告,不点名指控我是反马克思主义。因为我写的为邵荃麟平反的文章中,批判了“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英雄人物”的谬论,而他认为这不是谬论,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既然在为邵荃麟平反过程中有过这么多的麻烦,因此弄清此案发生的原委,还是很有必要的。
黎之同志是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干部,经常联系中国作协,有时列席党组会议。他也全程参加了大连会议。因此他是当事人,知情人,他提供的情况应该是可信的。他对此事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见于他著的《文坛风云录》,现摘要于下:
一、“我当时(指大连会议期间)的印象是,邵(荃麟)讲得比较全面、严谨、平稳。没有特别发挥‘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论点。”(第345页)
二、大连会议结束,黎之返京后,向中宣部文艺处汇报(1962年8月21日),“由于我对‘中间人物’等问题印象不深,未谈及这类问题。”(第350页)
三、“过了两天(8月23日),(分工管文艺的副部长)林默涵问我,听说大连会议上提出写‘中间人物’问题。我说荃麟发言中谈到,会上没有展开讨论。他说:他听周立波给他讲,会议开得好,提出写‘中间人物’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同前)
四、“9月5日林默涵让我把大连会议的情况写个材料,把关于‘中间人物’现实主义问题写一下,并让我把茅(盾)、周(扬)、邵的讲话拿来。——林默涵阅后批给周扬,周在他的名字上画了圈,退给我。”(同前)这里说的茅盾、周扬讲话,即指他们在大连会议上讲的话。
五、“9月22日林召集在京文艺报刊和各大报副刊负责人开会,讲了毛泽东提出抓阶级斗争的精神,布置检查。会上作为问题他点了‘中间人物’。”(第351页)
六、“九月号《文艺报》上发表了沐阳根据大连会议精神写的随笔《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自然成了问题。有一天,林默涵同张光年谈事,同时也提到这篇文章。林说:恐怕《文艺报》要再写篇文章,表明态度。张光年指着我说:“让黎之也写篇随笔,与作者商榷。”(第352页)
可见,从8月21日黎之向文艺处汇报,到9月22日林默涵公开点名,“中间人物”论已被定性为“错误理论主张”。整个事件是由林默涵同志发现、提出、定性、点名、公开,批评,在一个月里一手铸成。周扬自己与大连会议有关,曾到会讲话,表示支持,如今既未主动推波助澜去批邵,也未制止这种捕风捉影的诬陷,为邵说项,施以援手。
七、后来,据说“1963年底和1964年7月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后,江青下令让写出批判‘中间人物’论的有分量的文章”。但是,“邵荃麟从未正式发表过关于‘中间人物’的言论,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只有原始记录,并未经作者过目。为此,周扬、林默涵和作协负责人反复研究,只好由《文艺报》编辑部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和大连会议记录,断章取义,拼凑了一个《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写了一篇《‘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点名批判邵荃麟。发表在1964年8、9期合刊的《文艺报》上”。(第352—353页)
黎之此处所记的关键时间和情况有误。根据林默涵同志所说的事实应是:在毛泽东第一个批示传达后,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在整风中又揭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有人主张文学创作要着重写中间人物等等。中宣部就文联和各协会在整风中揭发出来的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见林默涵:《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然后,才有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才有《文艺报》对邵荃麟的大批判,并且升级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株连参加大连会议的十六位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以至会议的记录者都无一幸免,而受到批判和迫害。也就是说,所谓“中间人物”问题是中宣部、林默涵主动先向中央报告,提供材料,并且作为突出的政治问题上报的,而不是江青等率先主动发难的。
但是,黎之同志还记述了一个重要情况:即在上述毛泽东第二个批示下达后,中宣部开始搞文艺整风,林默涵负责评论组,指示黎之编印材料,共有五项:“1、对文化部意见。2、30年代问题。3、田汉思想、作品。4、中间人物。5、文联的问题。”(见《文坛风云录》第452页)可见这时林默涵已把他的一大发现当作五大重点问题之一,也是唯一的要着重批判的反面理论主张了。
“文革”以后,林默涵在1977—1978年间的一些会议上,多次谈到十七年文艺战线斗争历史,在谈及江青的《纪要》中诬陷文艺界搞“黑八论”时,他历数每一个所谓“黑论”包括“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的揭发批判过程,明确指出“这些黑论实际上都是我们揭露出来,批判了的,根本不是江青发现的,现在她却无耻地把功劳都抢了过去……”林默涵的这些发言内容为很多人所熟知,我自己就曾亲耳聆听过。当时就引起人们的议论,引为笑谈,说:“怎么与‘四人帮’抢起功劳来了!”林默涵这些发言又一次证实了诸如批判“中间人物”论是由他们当政时搞出来的。
1978年底《文艺报》编委会讨论我写的为邵荃麟平反文章时,林默涵的意见再一次明确证实:“中间人物”论是由他发现搞起来的。详情见前所述。
就在那次《文艺报》编委会上,林还说,邵荃麟曾是他的领导。他对邵荃麟是尊重的。他们之间个人关系也是好的。这更说明,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一案与个人恩怨无关,不像丁玲问题有历史的宗派的宿怨等等复杂因素;也不像胡风问题有毛泽东介入的因素;也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邵在“大写十三年”问题上与张春桥、姚文元等有过争论而结怨引发的;更不是“文革”一网打尽时才发生的。也许正因为这样,邵荃麟的冤案更值得人们反思,更有典型意义。
现在,我们能够选取的,关于发生这样的荒诞事件的原因,除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外,只能是:这是一个“哨兵”所为。
什么叫“哨兵”?那时的权威们一再强调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风雨表”;“文艺批评是文艺界主要斗争武器”;“某些文艺领导部门是哨兵”(江青就自称是“流动哨兵”);文艺界是战场,战线,是文化军队——在这种思想和机制指导下,有些部门和人员就负起“哨兵”的职责,掌控文艺界动向,用一种特殊的眼光和嗅觉去侦察、窥测异味,从字缝里寻觅敌情,向上秘密报告“狼来了!”简言之,把人民当敌人来对待。邵荃麟的所谓“中间人物”论被列为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理论主张,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我们还可以转换一个角度思考:知识分子本来应该从事自己的专业的创造性劳动,从而对社会作出积极的建设性的人文贡献,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等等,都是无例外的理应如此的。当然转业从政从商……都是正常的,也就另当别论。但是当你从事专门侦察同志同类同行同事的言行,并且不由分说地据此论罪……等等。这样,一方面形成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残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大批知识分子道德上人格上的堕落。其原因是出于自保,谋生,邀宠,还是思想极端僵化……?在中国那个特殊政治环境中,发生这样畸形的怪事,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它既不道德,也不符合法制。试想那时,连公安部门逮捕人都要作家介入,例如,反胡风时,作家刘白羽领着公安警察去抓捕作家胡风,作家黄秋耘领着公安抓捕冯大海(当时《文艺学习》编辑部创作组代组长),上海作家吴强领着公安抓捕作家耿庸……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他们都不过是奉命办事,有的当时内心就极不愿意,感到尴尬。但这样可怕而可悲的事情,在哪一部文学史上,哪一国的知识分子中,能够找到呢?就更不必说诸如深文周纳、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事生非、横加罪名等,更是有的知识分子之所长了。
邵荃麟万万想不到,他从年轻时就怀着纯洁的美好的理想献身革命,一生执著地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却仅仅为了几句关于写作方面的话,受尽折磨和迫害,最后,在“文革”时,瘐死秦城狱中。黄秋耘曾听与邵同狱住在对门的刘白羽说,邵临死前那晚,高声惨叫许久,“是由于疾病折磨,还是由于被拷打,他也不知道”。(见《风雨年华》第253页)
之前,邵荃麟被关在作协牛棚时,已重病在身。他还吃力地对黄秋耘说:“你给我想想看,我参加革命这几十年以来,有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同前第242页)这个忠厚诚实的革命者直到生命的终点,还在苦苦追问自己,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带着这个苦恼和困惑离开这个人世的,早在1964年批判邵的时候,《文艺报》副主编、评论家侯金镜就非常不解地不平地对黎之说过:像邵这样一个宽厚善良的人,“他得罪了谁?”(《文坛风云录》第354页)有一次,批判会后,黎之在大门口遇到邵,邵声音低沉地说:“黎之同志,你应该帮助我。”黎之听了,心头酸楚,几乎流下泪来。这样莫须有的冤屈,在发生之初,人们就已看得很清楚。人们的心底,都有一个疑问:这是为什么呢?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了邵荃麟在1943年翻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后写的《译后记》,他说:“为什么遭受损害?为什么遭受侮辱?这是苦恼着作者也是苦恼着作品中的主人公的问题,同时也是苦恼着当时俄国人民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同样又曾苦恼过译者,现在又还继续苦恼着我们。邵荃麟的悲情人生,还有许多和他一样遭遇的人,都给我们提出了这样苦恼的问题,使我们无法不继续追问,反思,寻找解除苦恼的出路,让这样悲惨荒诞的历史不再重复,让人民真正走上健康自由理性的大道。
这是我们的历史职责,也是我们纪念和追怀邵荃麟同志时应有的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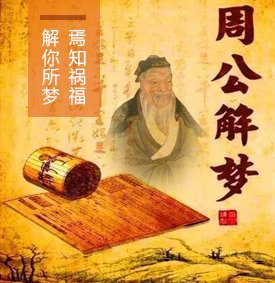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